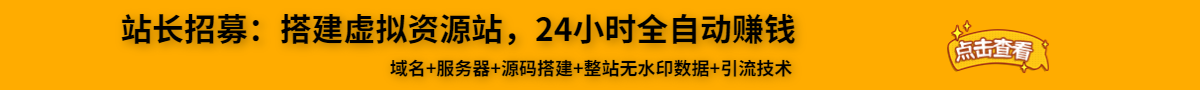【新书札记】

《西南记:北纬三十度的河山地理》书影。中国文史出版社供图
路灯发黄,行人渐渐少了,想来也必定是各有归处的了。庞大和茂密的榕树和银杏树叶掩映的楼房里,有些窗户还在亮着。远处不断传来车辆渐渐减少的呼啸声,一切都在归于沉寂。我坐在其中一条小街的一侧,背靠着一段围墙,其中是西南佛教名刹文殊院,之外是兜卖各种货品的文书院街,以公墓办事处和丧葬品居多,还有几家餐馆、茶楼、糕点店、蜀锦和银制品店。不知道多少人坐过的藤椅上油光发亮。杯中的茶早就淡了。我仍旧独自在这里发呆,内心漫无目的地想。这是偌大的成都市区,直到接近午夜的时候,我才起身,买单,往住处走。
再或者,我一个人,坐在万福桥的府南河边,沉浸在万千蚊虫之间,看着衔泥带沙的府南河,不知何往地流动。两边的灯光在河水中又制造了一个新的世界,虚幻、隐秘、透亮而又幽暗。这样的情景,持续了差不多一年多时间。那是2010年末,我从西北的巴丹吉林沙漠军营调到了原成都军区政治部文艺创作室,由此结束了多年以来写公文及其他一些行政工作,以军队专业文艺创作员和《西南军事文学》杂志编辑的身份,融入了这个我此前陌生的城市。
在此之前,我始终没有踏入过四川一步,最近的,也只是一次次地路过西安。也从没有想到,人生的某一天,我会来到这样的一个从不沾亲带故、地处西南、远离故乡的他人的城市生活。这非常蹊跷,充满戏剧性。单位就在北较场,没事的时候,我总是在周边转悠。起初不熟悉,走到大安西路就觉得很远了,到营门口也认为距离单位有了很长的一段距离。一个人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的所有行踪,其实是一个慢慢熟悉的过程,而个人的感觉,更像是一匹行走在满是人群和楼宇当中的孤狼。
西北巴丹吉林沙漠的空旷与幽深,人口的少,乃至地理环境的荒芜,长期的整齐划一与令行禁止,使得我对沙漠戈壁的旷达有了莫名而又深刻的依赖和信任,甚至不想改变。而城市于我的诱惑,仅仅是为了孩子读书环境好一些,长大之后省得再从西北往内陆迁徙。起初,我已经在河北老家买了房子,也想着,有朝一日回到老家的那座城市去,尽管,我很不喜欢那种促狭、小、眼界的窄与文化、思维上的故步自封,以及近乎赤裸的世道人情等。
这只是我当年在西北沙漠戈壁当中对故乡的一种个人看法,浅薄而又固执。及至我融入成都,一下子就被这座城市自身所具备且绵延久长的热闹与安闲气氛感染了。它的慢生活对于多年劳碌的我来说,是一种安顿。它的丰裕的物质环境又让我蓦然觉得了人生当中的某种富足,尽管这很外在,也需要更多的付出。它的多文化的糅杂的气息又让我觉得了内心的一种丰盈状态。比如我常去的文殊院,这座建于隋代的古刹当中,至今令人心生幽静与敬畏。我几乎每一天都在它的周边晃悠,有时候也会穿过去,到东大街或者更远的街道上去溜达,更或者,从五丁桥再转向宁夏街等地。很多时候,下班,我一个人沿着人民中路一直走到天府广场,再原路返回。
盛夏是成都最美的时候,虽然溽热难耐,但到处都很热闹。走在街道上,人群汹汹,男的女的,来来往往,一色的生面孔。相比在沙漠天长日久之后的人人相识,城市最大的特点是使得人走在其中,即使出丑,也不会传到熟人耳朵当中。成都这地方出美女,她们穿着时髦、新潮的衣服,以骄傲的神情或者平静的面容踏踏而行,罔顾周边的任何人。夜深人静的时候,坐在文殊院某个茶摊旁边,喝茶、看书、玩手机、想心事,直到夜灯空照,四下无人,远处近处的喧嚣渐渐有了稀释和终止的迹象,方才觉得,该回去睡觉了。
如此大半年的光景,我竟然没有去过近在咫尺的都江堰,雅安、南充、绵阳、广安等地虽说也很近,但对我这样的一个外来的异乡客来说,在心理上也觉得遥不可及。直到2012年春天,受朋友之邀,我第一次去了雅安,那里的碧峰峡、蒙顶山、二郎山,以及青衣江和岷江边上,对我来说都是极为新鲜的,也使得我第一次领略了川地的自然风貌。特别是在碧峰峡,第一次看到熊猫。这看起来笨拙的猛兽,很喜欢在高高的树上睡觉,抱着翠竹不断地啃食。
徒步的碧峰峡之间,清亮的流水和瀑布,葳蕤的植被和摇曳的花朵,使得我第一次体验到了蜀地的丰茂与温润。二郎山下的感觉也好,山谷之中,河流悠然,与当地的朋友们喝起酒来,也是极为畅意和快乐。似乎从这时候开始,我开始毫无计划地开始了对整个四川和西南地区的游历,这北纬三十度线上的河山地理,奇峻的峰岭、旷达的地脉,幽深的峡谷,诸多的遗址,包括其中的传奇和神话,历史与奇迹,自然是美不胜收,余韵悠长。之前我只知道都江堰和青城山,但不知其境内还有也颇为神奇、文化和仙道气息颇浓的灵岩山及其丰富的文化和宗教的蕴藏。我以为青城山为当地最高,殊不知,它的主峰则是赵公山。对于神奇的大地,想象力远远不够。那些显赫的、有名的,只是人所共知的一个名胜景点,而名声四周的那些存在,特别是物种的多样化、人群的生活习俗及现状等等,才是最真实最富有的人间意味与文化趣味。
如蓬溪县境内的小小高峰山,其上的传说,也值得玩味。开国元勋朱德故里,更能令人觉得了天地造化的神奇与偶然。阆中更是如此。那里出现的几个缥缈人物及其作为,令人细思若悟。至于横断山脉之中的康定、九寨沟、色达、九龙、汶川、茂县、黑水、若尔盖等地方,奇特地形之外,还有着相互杂糅与渗透的民族文化,流传久远的各色故事与传奇。其中,马尔康是作家阿来的故乡,到那里逗留数日,也似乎能够觉得一些为什么出现阿来这样的作家的一些难以言说的因由。还有平武的白马等地。至于广元,剑门关之于蜀汉乃至整个四川盆地的战略和文化意义,确实不容小觑,蜀道之于中原文明的融入,以及对古之西南夷的影响和渗透,无形而又有迹可循。
比如重庆的大足石刻,其雍容华贵与丰富雄厚,确确地令人叹为观止;再比如遵义的海龙屯,土司杨应龙及其祖上的荣耀以及最终的覆灭,也堪称一个有意思的文化和历史层面的现象;鸡鸣三省之地的红军遗迹与珍贵传说,可使得人联想起历史在关键时刻的神妙;贵阳云岩山上的阳明祠,是对这位哲学家和名臣的纪念;还有尹道真等人对西南地区的文化传播和教化之功,都是令人景仰的。在消失无踪的赫章夜郎国都遗址,我想到的是,从前的西南地区文化和境域的奇崛和广大,幽深与无尽。
最令人匪夷所思的,当然还是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不断的考古发现,使得这两处人类文明遗迹,焕发了更为迷离和深奥的复杂色彩。还有毗邻云南的攀枝花,充满高原气息的凉山州等地,我每次都是匆匆而过。如此十多年时间,我不仅没有走遍整个西南,就连四川很多地方也还没有去过。每到一地,我尽可能地仔细浏览和拜谒,在那些奇山秀水、镌刻在当地人心和文化史上的遗迹面前,也尽可能地谦卑。慢慢觉得,四川乃至整个西南地区,其文化上的独立与复杂,精神上的超脱乃至习俗当中的豁达与散漫、辛勤等等,都是与其他地域有着明显区别且富有鲜明特征的。
在我们这个星球上,北纬三十度这一纬线,普遍被认为是世界上最神奇的甚至是诡异的,金字塔、马里亚纳海沟、百慕大三角洲、英格兰巨石“雷线”、波斯波利斯古城、圣弗兰西斯科山脉岩画、巴勒贝克遗址、梅里雪山、泰姬陵、武当山、三清山等,还有三星堆、金沙遗址、怒江大峡谷和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等,构成了这一纬线上最为奇诡、宏伟、神秘的风景,其中很多文明遗迹、气候、自然灾害等,尽管人类发明了多种科技和探索古文明的方式,但对于大地这一本丰厚、幽邃之书,仍旧所知甚少。
相对于这些未解之谜和奇特现象,我关注的只是西南地区,乃至北纬三十度纬线上的一些山川地貌,以及无所不在的各种人类遗迹和文化遗留,也更关注人的历史与传说。我也清醒地认识到,一个人,无论怎样地穷尽所有与跋山涉水,探古说今,眺望未来,也都是自我意义的一种认知和判断,并不能囊括和代表所有人的感觉和看法。
就如同我的这本书命名为《西南记:北纬30度的河山地理》一般,记录的只是自己所到之处,以及个人在一方地域上的不规则的行走体验和观感,还有一些似是而非的感喟、联想与告知。一个人之于大地上的痕迹,有些看起来是大众的,甚至人类的,但最终也只能作为人类众多经验当中的一个构成部分。
祝福大地上的人们,都能在不断的游历中,一点点地找到世界的真相,尤其是我们内心和精神当中的那些至关重要的东西。(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获第三届冰心散文奖单篇作品奖、全军优秀文艺作品奖和首届林语堂散文奖提名奖等;本文经授权摘编自《西南记:北纬三十度的河山地理》一书“代后记”)
责任编辑:许革,张彦武
来源:中国青年报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