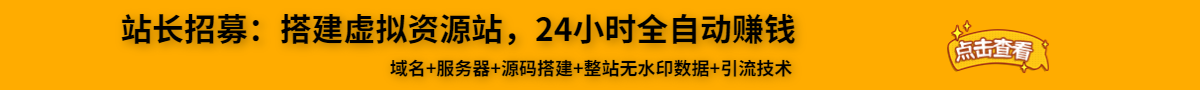作者 陈蔚文
听见几位朋友聊天。前阵子到柬埔寨,去了吴哥窟,没啥好看的,就是一些石头。就是,有些石头雕像还破破烂烂,不过柬埔寨的物价蛮便宜。我吃惊于她们对吴哥窟以及这些石雕的印象。
前几天有人在微信群里聊《安娜·卡列尼娜》:与一部通俗的情感小说之间没有多大的距离。安娜、渥伦斯基和卡列宁之间没有什么新鲜的故事,列文与吉提也是平常夫妻——所有的元素相加也没有办法把它划到伟大小说的范围之内。另一位作家说:什么样的小说才是好小说?故事、情节、人物以及结构,是不是小说优劣的最重要元素?如果不是,那究竟是什么?其实,我并不关注究竟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也并不关注情节进展,但我看见了列文、吉提、安娜、奥勃朗斯基、安德烈耶夫公爵、卡列宁、渥伦斯基……我听到了他们心跳,那种切入真实的力度与深度令后来者比如福克纳等都略显单薄,这就是为何海明威声称他打倒了所有前辈作家,但到了列夫·托尔斯泰这里甘拜下风的原因。列夫·托尔斯泰在他的时代做到了对真实的最大限度的开拓。
文学是见仁见智的,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但就这个对话,我同意后面这位作家。如从新鲜的故事角度考量,《红楼梦》也算是部通俗的情感小说,因为故事不新鲜,无非权贵之家如何从繁华走向败落,以及一对痴心男女的爱情悲剧。《悲惨世界》也可概括为一个有偷盗行为的穷小子,如何在仁慈主教的感召下改邪归正,从善如流,并发家致富,救助孤寡,完成自我救赎的故事。
或许,所有伟大的文学作品讲述的都不是那么新鲜的故事,至少不如一些悬疑或侦探、穿越小说来得新鲜。正如许多伟大的建筑从材质上来看不过是木与石,钢与土——然而,是什么使它们变得伟大?
譬如吴哥窟。
台湾作家蒋勋写过一本《吴哥之美》,他为此14次游历吴哥。当我到达柬埔寨,站在吴哥窟的石雕前时,我在想,是什么吸引蒋勋来了这么多次?在就是一些石头之外,他还看到了什么?蒋勋自己也曾有此问:吴哥窟我一去再去,我想在那里寻找什么?我只是想证明曾经优秀过的文明不会消失吗?而我的文明呢?会被以后的人纪念吗?
当年看电影《花样年华》时遂对吴哥窟有了向往,这部改编自香港作家刘以鬯小说《对倒》的影片讲述了一个关于迁徙的爱情故事。电影结尾,梁朝伟饰演的周慕云在吴哥窟对着一个树洞说出了心中的秘密,以草封缄。那个藏着秘密的树洞,是对人性的理解与体恤。它使柬埔寨这个地名从此有了一抹夕照般的温情。
当站在巴戎寺中,仰视那49座巨大的四面佛雕像,柬埔寨从文艺的温情转向了历史的厚重。佛像都为典型高棉人面容,这笑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那么静穆、祥和。这就是令吴哥窟蜚声世界的高棉的微笑——在这微笑背后,其实有更复杂的成分,因此蒋勋才会说:他们的微笑成为城市高处唯一的表情,包容爱恨,超越生死,通过漫长岁月,把笑容传递给后世。
他称吴哥窟为城中之城,是肉身里心灵的留白。也许这是他一次次来到此地的原因,思考建筑里时间与空间的力量,感受历史、信仰以及艺术的永恒魅力——正是这些同构了建筑的伟大。一座古建筑无论如何颓旧,其内在的文化内涵无法被替代。反之,一座仿古建筑无论在外形上多么神似古建筑,其内在的历史信息近乎为零。
旅行的精髓是一种流浪感,特别是在不同文化中展开的异域漫游,所以我们去到不同的地域,去观看、了解那些陌生的景观背后潜藏的文化密码,让那些异质的经验引领我们,扩充对这个世界的认知。
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正如一座经典建筑,它或许未使用什么新奇的建筑材料,但它在若干合力的作用下,撑持起了一个有灵魂的空间,再现了一个有温度的人类现场。
在内容或文体的求新求变之外,经典的属性应当有着根本广泛的人性,绝不空洞,它辽阔,一叶知秋,是回声,亦是追问与探寻。在那些恢宏而精微的细节当中,游走与驻扎着各式各样的我们。
如果列举出一百部名著,熟练的名著缩写者可以毫不费力地把它们整理成一千字内的提要或梗概,而这些提要,大抵是太阳底下无新事——那业已被写过无数次的人类生活,男与女,生与死,泪与笑,罪与罚,圆满与残缺……但显然,一支伟大的笔总是能以它充满力量的方式从容展开讲述,从亘古的旧中呈现新的阅读体验。
正如用无处不在的石头,可造就许多迥然不同的建筑,每一座都自成风格,其中的灵魂会对生命有真正的开启。开启的前提是——观看它的生命不能是漠然、封闭的,更不能恃傲慢与偏见。如此,景观——无论是建筑景观还是文学景观,与人之间才能相互看见与被看见。
《光明日报》( 2019年11月08日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