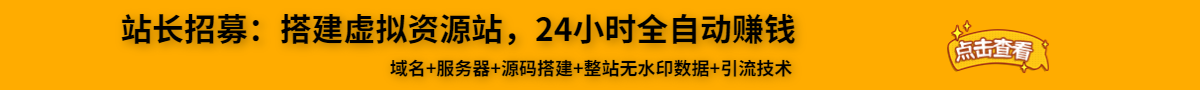我一直以为‘强奸’并不只是一九九二年的那晚在我那间学生公寓的地板上发生的事,它还包括在医院中的场景、事后在我脑海中不断重现的情景,朋友给我的慰藉,以及最后我大学毕业……随着我的写作的不断推进,我现在意识到‘强奸’还包括这次的逮捕和诉讼,于是我继续写下去。
在《女人无名》一书开篇的自序中,作者艾米莉·温斯洛这样写道。
1992年,当时还在匹兹堡上大学的艾米莉·温斯洛遭遇一名陌生男子入室强奸。2013年,当她已经在英国组建家庭,成为两个孩子的母亲,并走上职业写作道路之后,当年侵犯她的那个男人因涉嫌其他案件被警方逮捕。21年前那起不了了之的强奸案也因此再度进入了调查程序。作为一个侦探小说创作者,艾米莉怀着极大的勇气与好奇心,以旁观侦探的视角,对当年的罪犯弗莱尔展开了一场个人调查。她抽丝剥茧般拼凑出了罪犯的种种过往,同时将自己二十多年来的生活片段以及有关此案的庭审经历穿插其中,完成了这本《女人无名》。

《女人无名》作者、作家艾米莉·温斯洛
我们当然可以将《女人无名》视作一场对于姗姗来迟的正义的追寻,也可以看做是一位女性只身一人惊心动魄的追凶之旅。然而如果站在一个更为重要也更具公共性的视角上来看,我们或许可以把这本书当成一次对完美受害者文化的深度反思。当曾经的完美受害者——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一位在从洗衣房回家路上遭遇罪犯跟踪并入室强奸的处女——21年后重新走上法庭,她为人妻为人母的身份对于公众以及法庭对她的判断有着何种负面影响?这种负面影响来自何处?为什么犯罪者劣迹斑斑却苛求受害者纯洁完美?为何犯罪者定罪要取决于受害者的完美程度?完美受害者的逻辑是如何深植于社会文化体系甚至法律制度之中并持续运转的?
01
不完美的受害者:
走出强奸阴影的我算哪门子的受害人?
01
很明显,假如他们要给我的案子定罪,就得要求我成为一个完美的、内心破碎的小公主。我这么说完全是因为自己就是一个这样非常接近所谓完美的受害人:强奸案发生时,我是一个内心虔诚、头脑冷静的处女,现如今我已为人妻、为人母。但是,如果我说他干了我,那我就跟这样的完美形象丝毫不沾边了……我得装得跟个傻子似的,但又不那么傻,愣愣地一字一句地说‘他把他的阴茎放到我的阴道里。’这可真他妈的瞎扯淡。
在筹备正式庭审出庭作证时,艾米莉·温斯洛写下上面这段话。她道出了自己面临的一个困境——随着时间的流逝,在当她那完美受害者的保护层逐渐褪去之后,她究竟该以何种姿态站在法庭上,面对辨方律师的问询以及陪审团审视的目光?
之所以将完美受害者称为保护层,是因为它能够最大限度地激发社会公众的同情。挪威犯罪学者Nils Christie曾于1986年给出过完美受害者的定义。在他看来,一位在看望自己生病的姐姐的路上被一位滥用毒品的成年男性抢劫的老年女性具备了完美受害者的全部特质,这包括:
相对施害者而言,受害者处于弱势地位(受害者极有可能是女性、生病、很年长或者很年轻);
受害者起码在从事合情合理的日常工作;
对于发生的事情,受害者无可指摘;
施害者对受害者占据主导地位,并且能够用负面词汇进行描述;
施害者不认识受害者,也和ta毫无关系;
受害者拥有力量、影响力,能够成功言说自己的受害人地位并且获得同情。
如果按照上述标准进行衡量,1992年的艾米莉的确是一位完美受害者。她是白人、年轻处女,也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案发时从学校附近的洗衣房回家,走在自己的常规路线上;而对她实施性侵的人,在案发之前与她素不相识。可即便她如此完美,在各个方面无可指摘,袭击她的罪犯却仍然逍遥法外,直到21年之后因为其他案件被缉拿归案。可是此时,艾米莉已经并非一位完美受害者了。她已婚、已育,不再是那位不知道性爱为何物的纯洁女孩。

完美受害者的逻辑是如何根植于社会文化体系以及法律制度中并持续运转的?
为此她深感惶恐,她在上庭前一次次演练自己的言行举止,考量自己的穿着打扮。她想要化妆、吹头发、穿合身的衣服,因为她知道她要接受陪审团和现场旁听者的审视,那些人会想他当年为什么会对我动念头,他们在脑子里给我打分,看我是不是真值得他这么做。她要表现出一副很难过的样子,但是不能爆粗,看上去要悲伤且脆弱,但不能愤怒。万一人们认为我拥有太多幸运或幸福,或太过强大,他们可能就不觉得弗莱尔做的那些事对我造成了什么影响。他们会认为我应该不需要什么了,甚至也不需要让他受到惩罚了。
所有的重压都在艾米莉这位曾经的被害者身上。她需要通过自己的陈述和言行举止,来反证罪犯对她造成的伤害。这涉及强奸或者性骚扰案件的一个重要悖论:受害者需要通过确认和检验他人在自己身体或心理上留下的伤害,来确认对方的罪名。伤害的消退在证明受害者回归正轨的同时,也有可能为受害者带来无可查证的危险。
在阅读和了解匹兹堡东区强奸案审判的资料时,艾米莉找到了一段另一位受害人呈给审判庭的受害说明,其中描述了强奸对其造成的持续的身体伤害、职业影响、反复的自杀倾向、对性爱的恐惧、创伤后应激障碍以及长期的忧郁症困扰。她接着写到:读到这样的文章让我感觉有些害怕,这些症状我都没有,我算哪门子的受害人?能够从阴影中走出来,原本应该是一场胜利,但我怎么反而觉得让自己失望了。这种以我的恢复情况来衡量强奸犯的恶劣程度的标准,在我看来有失公平。就好像我恢复得越好,越能重新振作起来,他就越是可以得到宽恕,他对我所做的一切也越是可以被忽略。
要在舆论层面打破这种悖论,就要让公众了解:伤痛的缓解甚至消失,并不意味着施害者可以借此开脱免责。正如她在《女人无名》中所写:我该因此感谢他吗?我要感谢的是我自己,还有我的朋友们。他应该因为他的罪行受到审判,而不是以我应对此事所带给我的影响作为对他评判的尺度,这才是我想要看到的。同时我们也要意识到,Nils Christie提出完美受害者理论仅仅是一个假设模型。他指出,对于大部分受害者和侵犯者来说,他们并非完美的,他们只是普通人,他们会犯错,会判断错误,但这绝不意味着他们就应该被侵犯。

能够从阴影中走出来,原本应该是一场胜利,但我怎么反而觉得让自己失望了
媒体人吕频在其文章《女权者真被打脸了?》中也谈到了犯错的受害者。她认为,一些强奸受害者容易成为糟糕、失信的受害者,她们总是犯错误——没有正确和及时充分反应,遇事又不够勇敢果决,并经常自欺到最后一刻;事后又因恐惧情绪错过报警,又或者由于愤怒试图威胁对方。吕频写道,绝大多数犯罪都是因为受害者的错误或无能才能成功,也就是说,绝大多数受害者都是有问题的,这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一起犯罪行为成立的前提。
实际的调查数据也能证明这一点。根据斯德哥尔摩强奸救助中心的调查,70%的强奸受害人在遭受性侵的当时身体会无法动弹,无法表示拒绝,陷入一种解离状态,即紧张性强直静止(Tonic Immobility),通俗来讲,就是陷入假死状态。这种因恐惧而无法动弹的状况,绝不意味着受害者没有反抗的意愿,更不意味着ta们因此就应该被侵犯。但以日本为例,在对强奸罪进行审判的时候,质询的不是受害者心中是否有拒绝之意,而是这种拒绝之意有没有明确传达给嫌疑人。除此之外也有研究指出,在案例法中,庭审过程中对于被害人个人历史的挖掘,成为了性骚扰或者性侵案件中对于被害人可信度攻击的重灾区。
要求受害者完美无瑕本身便是无稽之谈,而谴责受害者思路中最众所周知的理论公平世界谬误更是一种极大的误导。这种理论假设世界是完全公平的,灾难不会无缘无故降临到一个人头上,只要ta行为得当,就绝不会遭受不幸,受到伤害的话一定是因为受害者本身有错。公平世界谬误将人置于真空状态,强调了个体的主观能动性而忽视了个体客观身处的权力结构与宏观制度。这也是一种新自由主义范式下原子化个体盈亏自负的假设,这一假设建立起了一种关于性暴力的个体化和私有化话语,而忽略了更为广阔的社会、政治和经济背景中结构性的性别歧视和权力关系不对等的问题。
02
勇敢的幸存者:
强奸不仅包括一次侵入,
还有挥之不去的记忆及无果的法律程序
02
完美受害者迷思造成的另一个负面影响,就是将受害者永远禁锢和限制在受害者的位置之上,哪怕已经走出过去、重新开始,ta在他人眼中也仍旧是残缺的、可怜的、永远活在阴影下的。人们会小心翼翼,在谈及这段过往经历时眼神闪躲、言辞闪烁,甚至直接避而不谈。这种处理方式实际上也是根植于完美受害者模型的——受害者被想象为脆弱和不堪一击的,仿佛一生都无法走出阴影。
艾米莉·温斯洛在书中也谈到了周遭朋友对她的看法:他们听说我的遭遇后都感到很吃惊,因为在他们看来,但凡有这样经历的人都不会像我这样乐观、外向……我很高兴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强奸其实是严重的犯罪行为,不仅仅是一个‘错误’‘误解’或是‘一场不愉快的约会’。但是,这种普遍的理解有时候也容易走向另一个极端,认为受害者不仅受到了肉体上的伤害,还因此遭受了精神上的永久创伤。她并不喜欢诸如此类的看法,并在书中反问道:为什么强奸不可以让我变得更富有同情心、更诚实、更能接受不同的情感呢?它让我变成了一个更好的作家,这是我现在从事的工作。

艾米莉与丈夫在1998年结婚
艾米莉所提到的人们对于受害人的极端想象,甚至深深根植于读者的阅读过程中。在跟随她一起追踪罪犯过往的人生经历,一点点将散落各处的细节与生活碎片拼凑成一幅完整图像的过程中,作为读者的我也常常感到诧异——为何一个曾经的受害者要如此执着于施害者,并对他的过往投入如此之大的耐心、决心与好奇心?为何她要一次次在谷歌搜索引擎中输入他的名字、追查他的照片、了解他的家人并试图拼凑他人生的时间轴线?为何她会写下知道他的名字,找到他的照片,这些对我而言都是一种馈赠。我正在打开这个礼物这样的语句?在某种程度上,这句话令人毛骨悚然。馈赠——那些过往的伤害、那些持续的疼痛、那些对她生活造成举足轻重影响的线索——怎么会是一种馈赠呢?她是否并不像她在书中所描述的那个自己?她是否从未走出过这段经历,以至于在长达21年的人生里始终活在这起强奸案的阴影之下,以至于她的一言一行、她的每一个人生选择都和这个罪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是不是一种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
当我再转念一想,这种想法是否也落入了完美受害者的陷阱之中呢?为何在我们的认知里,受害者这个标签就是一生都无法摆脱的?为何曾经的受害者不能彻底摆脱过去、开启全新生活?为何一位受害者对施害者展开追踪调查的出发点不能是极大的写作热情与好奇心,而一定是PTSD?
这也是为什么在对待性骚扰的时候,有些人主张不要继续使用受害者(victim)来称呼ta们,而要将ta们称为幸存者(survivor)。从受害者到幸存者,往往意味着一个个体从过往的伤痛中走出来,也意味着有足够的勇气和能力开展新的生活。而如果个体已经做好准备重新开始,周遭的亲朋好友和社会舆论又有什么理由加以阻拦?我们为何要一直被完美受害者的理论绑架与胁迫?
在《女人无名》的结尾,在艾米莉·温斯洛做好了万全的准备、即将要打一场漂亮仗的时候,她被告知,按照修改过的州法律,她这桩旧案的诉讼时效已经过去。当年对她实施强奸的阿瑟·弗莱尔自由了,但他的DNA数据仍将保留在联邦调查局的数据库中,只要其他案件有任何全新或者最新处理的证据出现,都会被拿来进行比对。这并不是我们预想中的光明结局:罪犯绳之以法,正义终得伸张。

《女人无名:20年追寻真相和正义之路》[美]艾米莉·温斯洛 著 徐晓丽 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9年4月
但这却符合强奸案件的常态。全美性侵热线等机构所做的一项调查显示,在1000起立案的强奸案里,大概只有200多起是受害者报告给警察的;在进入到警察调查环节后,大多数案件的警察会认为证据不足以实施逮捕,大概只有40多起会逮捕嫌疑人;嫌疑人被逮捕后,如果审问不出东西,就会被释放;审问之后,案件会移交给公诉人,由公诉人决定是否要起诉;即便起诉,原告也不一定能赢下案子。因此在1000起强奸案中,走完以上流程、受害者能够真正上庭并且赢下来的案子,大概只有5起。而强奸犯被缉拿归案,很多时候也并非因为强奸,而是因为其他类型的案件。因此,法律并不意味着绝对的公平与正义,但未被绳之以法也不代表罪行没有实施,也绝不代表伤害没有造成。
正如艾米莉在自序中所说的那样,强奸不仅仅意味着一次侵入,而是包括日后那些反复到来的挥之不去的记忆,以及之后可能旷日持久又无疾而终的法律过程。类似地,从受害者到幸存者的过程,也不仅仅意味着身体和心理伤害的消失,它还意味着亲人朋友乃至整个社会文化的支持与理解,意味着在事发之后不要对受害者轻易指摘,意味着不要落入强奸文化的陷阱,将强奸归咎为个体疏忽与不小心而非结构性的性别暴力,更意味着当受害者渴望并且最终得以走出伤痛时,我们不要再将其禁锢和封锁在那片阴影之中。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撰文:傅适野,编辑:黄月,未经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授权不得转载。

未经授权谢绝转载
欢迎转发至朋友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