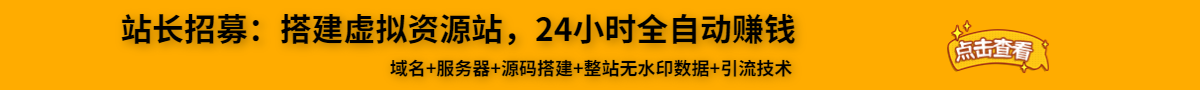文 | 赵晨
《咆哮》,一部名字听起来很像《权力的游戏》兰尼斯特族语——听我怒吼(Hear me roar)的Apple自制剧。光看剧名还以为剧集主创们有要么让她发声,要么听她咆哮的烈烈野心和熊熊斗志,然而剧情却被雄伟的标题映衬得出人意料的平淡。

此剧根据爱尔兰80后作家Cecelia Ahern的同名小说改编而来,选取原著中的八篇拍摄,每集30分钟,短小平淡,颇有小品文之风韵,正是贯彻宇宙之大,苍蝇之微,皆可取材之旨。老舍先生曾对此下过一定义:小品文,Essay,意思是投掷,像小儿投钱游戏那样,一下儿便要打着。无论它讲说什么,它总须一击而中,所以它是文艺中的小品,小文章。小,可并不就是容易。
既要轻松又要一击即中,是对剧集纵向平衡与深度挖掘的考验,《咆哮》选择从她入手。
标签预告带来匠气
首先是视角的高度统一,一至八集均贯彻了片名即主角的原则,她们分别是消失的女人,吃照片的女人,摆在架子上的女人,身上有咬痕的女人,被鸭子喂食的女人,解开自己遇害之谜的女人,退回丈夫的女人和爱马的女孩。不难看出,这是一次关于她的命题作文,八则故事的主语和关键词都是她。

女性写作、女性导演、女性主角的三方合力聚焦不同境遇中的她们,不再将她限缩于被凝视的单一境遇中,而是突破男性视角对女性的想象与限制,从她的经验出发,塑造她的形象,讲述她的故事,发出她的声音,深入挖掘她的内心世界。
1975年,劳拉·穆尔维的大作《视觉快感与电影叙事》诞生于女性解放运动的大潮流中,借助精神分析理论和父权制秩序两组资源展开。劳拉指出在主流的电影叙事中包含以男性为中心的视觉快感,父权文化贯穿其中,镜头与男性凝视的目光同构。论文发表40年后,NECSUS杂志曾组织女性主义电影研究三人谈,再次请回劳拉,结合自己长期的学术经验与写作实践,她指出女性主义的研究视角应该放在当代而非历史时期。此外,当下的女性主义不仅在学术意义上,还在更广泛的社会、文化、政治意义上回归。循着劳拉的视线观望《咆哮》,不难发现这部稍显平淡的剧集在塑造女性主体、表达女性困境、构建剧集与当下的关联、扩充女性主义的边界这几点上付出了可观的努力。

除了女性性别这一个同类项,简单提炼一下八集的关键词,分别是:族裔、回忆、凝视、平衡、PUA、仇女、物化、复仇。都是分量不轻的词汇,而这些重压词汇却环绕在女性的生活中,以她视角展现这些房间里的大象无疑更为直观。借助日常生活这一在女性主义第二次浪潮中被重新发现并在第三次浪潮中崛起为中坚的精神价值领域来呈现这些困境,力破主义与思想本身无法规避的形而上气质亦是踊跃尝试。
但是剧情的硬伤也由此而来,明确的标签使得演员和剧情都囿于完成标签,揭下标签之后人物的立体度和层次性大打折扣,与生活的关联度也稍显生硬,由是剧情过于直接明晰的现实指涉显出三分刻意。剧集中每一个单集的成功与否,也就取决于如何化解这种由标签预告所产生的匠气。
寓言套困境
显然,这是一部概念大于情节的剧集。但是这并不令人厌倦,因为剧集将女性生活中所遭遇的八种困窘境遇以寓言的形式呈现出来,从而顺理成章地预演了该境遇的极端状况,以作警示。寓言是一个经典的诗学概念,按照柯勒律治的判断,此概念包含将抽象观念转化为图像语言的意义。影视媒介无疑是展现图像语言的最佳媒介,借助帧幅完成言意同构,但是,要在三十分钟内将这些抽象的概念、沉重的意义以影像形式展现出来,并且不悬浮,难度系数颇高。新瓶装旧酒,寓言套困境,这是《咆哮》的突破路径与显著特色。

第一集,黑人女性在公务会谈中被一帮白人男性忽视,以至于明明在现场的她像是消失了一般,用消失寓言展现被忽视的境遇。
第二集,儿子即将离家,母亲患病偶发失忆,女儿与母亲的身份合法性受到双重挑战,她吃下照片便能找到过去的回忆,由此照片成为回忆的表征。剧集中还提到游戏《塞尔达传说》,亦是对回忆的指涉。
第三集,典型的娇妻养成记,女性放弃工作嫁人,被困在家庭中的一个架子上。格奥尔格·西美尔曾在《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一书中如此写道:金钱婚姻似乎是一种慢性的卖淫行为,婚姻中金钱操纵的那一部分同等程度内在地剥夺了人的——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的——尊严。被摆放在架子上的女人是被摆放在金钱筹码上的人,是被剥夺了尊严、被彻底物化进而沦为展览品的人。

第四集,工作家庭难两全的超人妈妈,难以负荷的抽象精神重压以皮肤疮疤具象展露。
第五集,生活屡屡受挫的单身女性在一只鸭子身上找到了情感依靠,跨物种的爱恋也逃不过异性对女性的规训与控制,煤气灯效应在生物界的全方位显灵。
第六集,以超现实的手法完成阴阳之我的共同在场,揭示男孩因仇女而起杀心的真相,展现生死两极间的女性困境。
第七集,丈夫成为和衣服鞋子一样的商品,有标价可退换,与第三集彼此呼应,物化的两性寓言。

第八集,探讨以女性身份如何面对复仇这桩精神伦理事件,同时以马揭示女性性别奥秘。
——梳理之后,不难看出剧情并无惊世骇俗的内容支撑,也没有令人目瞪口呆的价值输出,有新意但不出挑,有倾向但无立场,是一部奉行中庸之道的女性小品文合集,点到即可,过多不谈。
在本雅明这里,寓言不仅是修辞学概念,而且是看待世界的一种方式。在颓败的现实境遇面前,寓言的功能在于此间蕴含忧郁的碎片、反抗的火种以及威胁的武器。如果从这样的层面来理解《咆哮》的中庸与平淡,可将其视为平静的申诉,而不是歇斯底里的呼号。意图是让观众看到存在的问题,而不是提出解救之道;目标是警示观众形势严峻,而不是割下异性的头颅点火欢庆。因而《咆哮》既是独像的专注呈现,又是群像的众声和鸣。将每一集的寓言指涉聚集起来,可以听到剧方的发声:女性依然身处各种各样的困境,不要忽视。

女性主导自己的表达
那么平淡和中庸是否意味着《咆哮》不值一提呢?并非如此。当代法国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大师之一皮埃尔·布尔迪厄认为:‘老生常谈’在日常生活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所有的人都可以接受它,并且是在瞬间接受。是的,内容和题材的平庸恰是老生常谈的最佳注释,既然女性的生活中充满诸多困境,并且未得到改善与帮助,让更多的人看到,才能谈论下一步,即如何解决。既然有人不听不看不管不顾,那就不断地言说,一种唠叨的美学在诞生。
近年来,探讨女性人格,描摹女性精神的剧集已不少,《使女的故事》《大小谎言》《永不者》都是典例,荧幕上的女性形象日益多元,女性故事图景逐渐蔚为大观,随之浮现的女性问题亦层层堆积在观众面前。因此,《咆哮》存在的问题也是整个社会文化存在的问题,无路可走的结局和中庸的表达不该是我们对《咆哮》的怨怼,而是对大环境的质问与怀疑。《咆哮》还不是呐喊,而是上下求索的彷徨,一种温和的尝试,不以性别的二元对立映照女性自身,而是在女性视角下呈现女性经验,表达女性境遇,展露女性精神。由此,咆哮也是一种姿态,关乎探索与交流。寄沉痛于平淡,隐深思于留白,留白处正是你我着墨之地与努力之境。

此外,这并不是妮可·基德曼第一次担任制作人,上一次是《大小谎言》,依旧是全女性阵容,依旧探讨女性问题,依旧是成绩不俗。肉眼可见的是女性精神深度的扩展,女性角色人格层次的立体呈现,林心如担任制作人的《华灯初上》以及贾静雯担任制作人的《妈,别闹了!》也沿着这一路径继续前进。女性主义于这些制作人而言并不只是一个单薄的口号,而是切实的生存体验和生命际遇。

《我的天才女友》第三季中,莱农让自己的女儿不要看《包法利夫人》,原因是书里到处可以看到男人眼里女人的样子,女人提出的观点也被男人当成写作素材。事实的确如此,女性主导、自己表达,虽然并不一定都是十分佳品,但必然会为影视世界增添另一种表达的可能。正如影后弗兰西斯·麦克多蒙德在2018年奥斯卡颁奖典礼上的所做所言,她邀请在场所有女性的提名者、电影人、制作人、导演、编剧、作曲家等人起立,这个著名的罚站事件让当晚的投资方与制作人进一步看到了女性的存在及其身后的力量。最后弗兰西斯以Inclusion Rider两个词结束了自己的感言,这指演员在签署合同时可加入的一种多元包容条款,以确保电影制作过程中的性别和种族平等。这不仅是影后的感言,也应是普通女性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