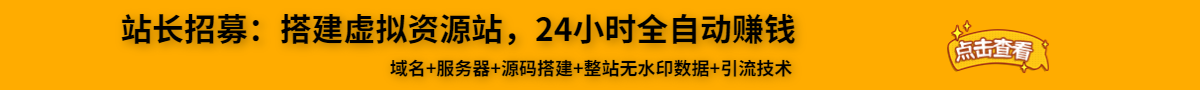疫情仍在持续,将人困居室内,读书不免多份随想,生活陡增一份沉思。如何在被动的生活中安放自身,成为我们当下的日常课题。在这种被动的生活方式下,有人借机重新看待琐碎的日常,有人乘隙细心凝视遗忘的角落,也有人在百无聊赖下开始莳花种草,还有人在夜间难眠时回想往昔。无论楼下花草的盛开还是凋谢,抑或床头图书的翻开还是合页,总有某些瞬间让我们在回望与展望之间获得某份宽慰或焦躁,毕竟日常生活才是我们最难抵抗的兵荒马乱。在本次回函之中,严步耕与王晓渔依然从日常的细节与读书的随感出发,谈论着这个酷暑难当的夏天……
晓渔兄:
“时间永是流驶”,但很多正常的,也会变得不正常;很多不正常的,都会变得正常起来。我们这里暂时变得正常起来了,连小区物业都以此为借口解散了核酸时组建的业主群,便可以避免业主每天在群内喷物业。毕竟,很多事情,除了口诛笔伐的吐槽之外,只要像物业一样眼不见,心也就不烦了;再多的事儿,也不会真的有事。太阳照常升起,日子依然得过。借用兄引用的托尔斯泰之言:一切都那么的“通常”,下楼方知花已被风吹雨打去,小区里的樱花就被我错过了花期。
在全面解除之后,我每天都会夜间独自散步竞走一番。我所居住的地带,旁边躺着三四座湿地公园,趴着诸多预留出来的绿化地带。白天鸟鸣夺喧,夜间虫蛙竞声,像是久违的老情人般喋喋不休;不过,在封步固足之后,我也想在暗夜里听听它们的唠叨。
万物皆刍,橐籥奈何?经常性地,一人独逛,灯灭方回。就像久别重逢或不曾照面的情侣恋人,恨不得一次性看个遍、听个够,或没完没了地把憋在心底的话语全都抖落出来。抑或,哪怕不启唇角,静默无言,便知双方想说什么,也让人感到某种幸福的满足感。毕竟,室内流亡般久了,近在眼前也变成远在天边了;当然,有些人有些事,远在天边也似近在眼前。
兄每次在信函中都会写到楼前的石榴花,有点像我每天都会不时眺望艾溪湖。这让我想起米兰·昆德拉的《无知》。整部小说读完后,可能是理念太像殖民地扩张之势,反而少了文学阅读后的韵味;最让我动容的反而不是小说主题,而是两位流亡者在面对眼前之景的柔软与谦卑:
女主人公跟重病的丈夫在法国外省,驻足桥头望着河水静静流淌,远处倒伏的老树在陶醉地开着花儿,高音喇叭突然爆出的喧嚷打破了她的沉浸,她顿时为消失在眼前的世界而泣不成声;男主人公回到布拉格后开车闲逛,在田间望着天边丘陵的繁茂林木,看着小路两旁夺艳的蔷薇,想到在自己生活的空间里,捷克人曾两次为了使这片景物永远属于自己而献出生命,这位冷漠的流亡者心中突然被唤起了怜爱,激动得也想让自己哭上一番。

米兰·昆德拉作品系列
在兵荒马乱的日常生活中,琐碎记忆是最后的避难所,让人能够安放自身、寻找方向。当这座避难所都丧失了,我们还剩下什么?就像那些花花草草,那些石榴金桃,在慌乱迷茫的日子里,认真对待它们,好好关注它们,嘴角总不免会自动上扬。琐碎的记忆,废话的瞎扯,同样也是如此。
那些风景,也是我们日夜守候的生活,我们为之奋斗的东西,不管是爱情的甜蜜或苦涩,不管是生活的艰辛还是幸福,守候它们就像是在守候一份真情一样。毕竟,最大的兵荒马乱往往存在于生活本身。睹物思人,人不在身旁时,那些东西也会让岁月变得可爱,安抚着一颗颗孤独而敏感的内心。无聊的废话或熟悉的风景,都可能关乎美好,它们就是日常生活里的崇高之所在。
近些时日,南方雨季,夜雨后醒来,窗外阳光明媚;打开窗户,满面清爽,楼下鸟鸣,清脆得可以啄破空气。这等天气,既不黏稠,也不闷湿,也不燥热,晴爽俱佳,让人心情大畅。每次走在外头散步,总喜欢看车水马龙,总喜欢看跟前走过的那些人。又或者,仰头看着遥远的闪烁的星星,像是在遥远的星空跟我打招呼,不会言语的它们就像借助闪烁,会心地回应着我的眼神。如此,便不会觉得天地太大、大地寂寥。前几日深夜子时,在小区楼下石凳躺着看天,明灭不定的星星夹在两栋楼之间,像是组成了一条银河似的,让人恍惚感到太不真实,内心却又觉得那般美好。
此时此刻,已是深夜四点多。22楼南阳台远眺,树木守护着街灯,街灯也照亮着树木,黑夜里隔几步路,就是一丛草绿。彼此之间,互相守候,真是美好,羡煞在楼上看风景的人。习惯凌晨入睡的我,想起在北京时的某晚,喝得太多而在茶馆睡了一宿。醒后打车回家已是四点多,天竟然就亮了。江西比北京天亮得晚,恍惚之间感觉:酒比天高,夜比梦短。高纬度的夜空,跟岁月一样,太容易催人老,因为天亮得太早。宿醉过后,句子敲门,不请自来,未邀而至。又是一个美好的生活景象。
在信函中,兄由景转入托尔斯泰,这位辨识度极高的俄国文豪,总让我想起茨威格对他相貌的描述。如果借用布罗茨基将奥登的脸庞比做“杂乱的床铺”,托尔斯泰那张“包含着整个俄国”的脸庞则像“原始的林莽”:“他的脸上,杂草丛生,树木密布:林莽多于空地,向内窥视的每个通道全都遭到拦阻。族长式的浓密虬髯迎风飘舞,一直向上挤进两边的面颊,遮住他那性感的嘴唇几十年之久,盖满了树皮一样龟裂的皮肤。手指一样粗细的两道浓眉像树根似的纠结在一起,头上杂乱的浓密头发泛起灰色的海浪,汇成骚动不宁的浪花。这乱成一团的头发,直如热带植物,到处纠结,无比浓密,似乎从史前时代一直繁茂生长。”

《茨威格精选集》作者:(奥地利)斯蒂芬·茨威格 译者:张玉书 等 版本: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9年11月
当读到兄引用托尔斯泰书写“起风前的暗流”时,看到他写的那个“普通的周末”,又让我想起茨威格笔下那个“美好的夏天”:“一九一四年的那个夏天……从来没有像今年这么美,而看来会越来越美,我们都无忧无虑地看着这个世界。至今我还记得很清楚,我在巴登的最后一天同朋友走过葡萄园的时候,一位种葡萄的老农对我们说:‘像今年这样好的夏天,我已经长时间没经历过了。如果今年夏天一直这么好,葡萄收成将比任何年头都好。我们会永远记住今年的这个夏天!’这个穿着蓝色酒窖工作服的老头,他自己不知道,他说的这句话千真万确。”
那一年,茨威格三十二岁;而重读《昨日的世界》之时,我也恰好在三十二岁。三十二岁的他,在那个“美好的夏天”里认为,“如一切顺利的话,在阳光灿烂的夏天,世界会变得更美丽,更合乎情理,就像一片可喜的庄稼。我爱这个世界,期望它有一个美好的现在,一个美好的未来。”但,“萨拉热窝的一声枪响”,刹那间把那个“昨日的世界”,“像一只空陶罐一样击得粉碎”。相同年龄的撞击,让我内心更添一份莫名的感受:只是,茨威格在巴登的葡萄园里听老农谈论着美好的收成;而我,却在室内的夏威夷竹前问着自己:是否,我也会记住这个夏天?我想,应该会的。
如同卡夫卡的青年时代一样,我“无辜的脸背后”同样“藏着一个巨大无垠的心灵世界”,只能“从心理上武装自己”才能躲避日常的兵荒马乱。这总不免让人怀旧起来,也让人对未来的道路一半犹疑一半激情。不过,我又会想,一切风平浪静之后,是否也会像茨威格那样想起“枪响前”那个“美好的夏天”?如果真的把自己流放后再归来,是否也像马尔科姆·考利那般想起“干草的气味”:
“转过一条肮脏的小路或突然出现的山顶,你的童年就显示在眼前:你一度赤脚玩耍过的田野,亲切的树木,你用以品评其他景色的美景。……出发到天知道的地方去,及时回家吃晚饭。……干草的气味真好闻,在谷仓里躺在干草堆里使现在和童年之间的岁月消失了。……现在谷仓已不复存在;有一年他们砍伐了铁杉林,原来是树林的地方只剩下残桩、枯干的树梢、树枝和木柴。你回不去了:他的童年之乡不复存在,而他又不属于任何其他地方。”

科尔姆·考利的《流放者归来》与布罗茨基的《水印》。
又或许,像布罗茨基在《水印:魂系威尼斯》中所写的为了逃离“前世”来获得“今生”那般来安慰自己,“为了拥有另一种人生,我们应该结束第一种人生,而且这个活儿应该处理得干净利落。没有哪个人能够令人信服地实现这种事,尽管有时,不辞而别的另一半或是政治体制确实会帮我们大忙”?
当然,布罗茨基用它的经验这般告诉我:“没有哪个人能够令人信服地实现这种事”……
严步耕
2022年05月21日 窗外重现马咽车阗之象
严兄:
看到兄写信是在凌晨四点,我有很长一段时间也是昼伏夜出。如果早晨要外出,只能半睡半醒地躺两三个小时就起床。想调整为常规作息,却总是失败,最大的难题是午睡:没有午睡,精神恍惚;一旦午睡就是两三个小时(特别羡慕午睡一刻钟即醒的“特异功能”),久睡伤神,醒来不仅疲惫,更是没有缘由的情绪低落(如果被闹铃吵醒,同样如此)。于是,陷入一种循环:好不容易早睡早起一次,多半会有疲惫的午睡,因为有午睡,晚间没法早睡,又回到晚睡晚起的状态。虽然晚睡晚起,那时的睡眠很好,有一个上午在昏睡中接过四五个电话,每次接完电话倒头就睡,不像现在,早醒后很难再入睡。
将近四十岁时,开始熬不动夜了,以前是夜间读书写作,逐渐夜间无法写作,再后来夜间读书也很困难。随着精力不济,睡眠慢慢调整为早睡早起,睡眠的能力也在降低,每日减少了两三个小时,很少再有午睡。
兄说到《昨日的世界》。或许是阅读的时机不同,我现在偏爱情感没那么强烈的文字。茨威格先生笔墨浓烈,笔下的维也纳和他的青春仿佛灿烂的午梦,我读时反觉得有些遥远,尽管能感受到他对“下沉年代”的痛切。
对于“昨日的世界”,我也偶有怀念,怀念时总会想起“失掉的好地狱”——鲁迅先生的一篇文章标题。“昨日”是复数的,“昨日”与“昨日”互有因果,也常有冲突,怀念哪一个或哪一些“昨日”?怀念“昨日”有时是对今日的疏离,可是“昨日”之中常隐藏着今日之因,如何做到怀念因却疏离果?“昨日”之中包含着不同个体的记忆,也包含着时代的集体记忆,每种记忆都包含着相反的因素,不必各打五十大板,但“昨日的世界”是否将“昨日”单一化了?如何区别昨日的青春(侧重个体的怀旧)与青春的昨日(侧重对时代的怀念)?怀念理想主义的时代,是不是会成为怀念自己的理想时代?忆甜思苦,会不会是另一种忆苦思甜?不过,日常的感慨不必如此条分缕析,否则也太累了。
还是谈谈日常。闭门不出的时候有过一些“报复性消费”的想法。可是在此之后,“报复”的念头不知去哪里了。以买书为例,我曾每年购书数百种。可是今年,我只在犀牛书店买过一次二手书,虽然购书网站的收藏夹里新添了不少条目,却没有下单。前后将近五个月未买新书,从读大学至今近三十年的时间里,从未有过。为什么会这样?我一时也无法解释。只是形势再度有些紧张,时有朋友或社区的楼栋因为密接被封控时,对于可能到来的再度封控,心态安定许多。
或许,没买新书,部分是因为近年来我主要在补读或重读一些经典,那些经典大多数手边已有。
兄此前说到闲时喜翻日记,我也有此好。有次翻看《曾纪泽日记》,每日都是看某书若干叶、习字若干纸、写对联若干副,观某某象棋若干局,与某某围棋若干局……感慨其父教子有方,又觉无趣。

《曾纪泽日记》作者:曾纪泽 整理者:刘志惠 版本:2013年12月
不知为何,他这些无趣的记载让我难忘,渐觉此种“日课”正为我的良药。我读书常随兴致,喜欢一口气把一本书读完,或者读了几页读不下去就扔到一边。然而,读经典是很难“灭此朝食”的。《道德经》仅五千言,一个下午甚或一两个小时就可以读完。可是,那么仓促读完与不读也没有什么区别,徒增“读过”的虚荣。记得豆瓣网站有过虚拟的图书条目,一本根本不存在的书,有不少热心读者做了“读过”的标记。
曾纪泽先生观棋下棋都要记下多少局,我难以效仿,惟每日读书可勉力为之。近年我渐以日课的方式读经典,放慢速度,每日只读若干页:哪怕读得愉快,也不多读;不轻易放下不读,哪怕读得不愉快,也尽力完成每日的页数(实际仍常有停顿)。在状态较好且未有繁事缠身时,可同时读三五种经典,视难度,每种少则十页、多则三五十页。经典通常是有难度的(哪怕似乎很容易懂),只读一遍很难称得上“读过”,需要反反复复读,最好是与友人一章一章甚或一页一页讨论过。
人文的魅力是“祛魅”,我对经典没有崇拜,也没有读完所有经典的抱负。听说有读者把经典分出等级,读过自己认为最高级别的几本经典,俾倪他人。经典变成了板斧,好玩又好笑。每部经典都是一个黑洞,如果被黑洞吸附,经典就成了压抑性的力量。
我读经典,主要是围绕自己的问题意识,进行自成脉络的阅读。读一部经典,会阅读相关研究著作,但与成为研究者不同。读《后汉书》,是对其中的文体有兴趣,不是要成为《后汉书》研究者。在古典中,我爱读六朝前后的部分文章,没那么正襟危坐,也没有绚烂浮辞,常引入口语的活水,有紧张有从容。《后汉书》《世说新语》的注,常有一些比正文还要生动的引文,可惜引文来源的典籍大都已经佚失。
与读书相比,对周边的事物,我几乎是一无所知。今年四月份,法国导演雅克·贝汉去世,他曾用许多年拍摄一部仅有七八十分钟的纪录片《微观世界》,呈现昆虫们的世界。屎壳郎推粪球原来那么可爱——在目力所及的世界,隐藏着多少秘密。有次路过紫荆丛,提醒自己稍稍停留,紫荆花去叶生,叶上有朝雨残存,一只苍蝇伫足其间。那时并不觉得苍蝇可厌,想起小林一茶先生的“露水的世,虽然是露水的世,虽然是如此”和“不要打哪!那苍蝇搓他的手,搓他的脚呢”(周作人译)。只是看到的时候,我把两首混在了一起,记成“露水的世,那苍蝇搓他的手,搓他的脚呢”。
今天看到一朵月季,晒得皱如木槿。想来你那里也很炎热,兄多保重。
晓渔
2022年7月21日至24日于暑中
作者/严步耕、王晓渔
编辑/袁春希
校对/柳宝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