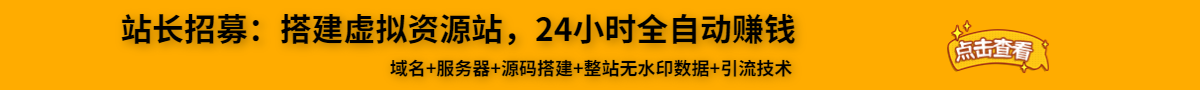西方传统经济理论认为劳动力流动可以实现劳动力及其附载要素在空间与区域上的有效配置,并有助于缓解贫困,熨平城乡和地区差距。然而,观察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大规模劳动力流动、贫困以及城乡关系演进中的典型特征化事实未必如此,值得关注。
(1)劳动力流动并未缩小甚至扩大了城乡和地区差距,同时带来了农村和欠发达地区人口结构的“畸形化”,“空心村”现象加剧等社会问题,进而影响减贫的潜在效应,农村贫困问题依然突出。(2)劳动力流动带来了贫困由农村和欠发达地区向城镇和发达地区的“空间位移”以及贫困在空间分布上的动态变化,这无疑对我国所实行的聚焦贫困区域和贫困村并实行就地开发的扶贫政策形成了考验、提出了新的要求。(3)大规模劳动力的外流刚性导致了横亘在农村与城市二维空间之间典型的“城乡接合部”“城中村”等第三维空间的形成和持续存在,限制了城乡深度融合。


原文 :《充分发挥劳动力流动的减贫和城乡融合效应》
作者 | 南京审计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樊士德
图片 | 网络
劳动力流动提升了农村家庭绝对收入
如何通过新的顶层设计、制度安排和政策调整,在劳动力合理流动、缓解贫困和城乡深度融合发展间找到有效的平衡点?为此,笔者于2016年和2018年对全国东中西三个地区的代表性省份进行了微观调查,收回有效问卷6370份,尝试探讨上述问题。
从全国范围来看,劳动力流动既提升了农村家庭绝对收入,又降低了收入贫困的相对概率。从家庭所在地村庄特征来看,自然灾害频发区及丘陵地区、高山和高原地区的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相对较低,贫困发生概率更高,而周围有企业、矿产资源及属于平原区或渔村的农村家庭则相对富裕,陷入贫困概率更低。从户主特征看,户主年龄与贫困发生率呈现 U 形关系,年轻或年老的户主家庭贫困发生概率显著增高;户主健康状况较差的家庭贫困发生概率显著增大;户主受教育年限越长的家庭贫困发生概率显著下降。从家庭特征看,人口规模、家庭老人比例、家庭儿童比例越大的家庭,贫困发生概率都显著提高;但有非农经营的家庭,贫困发生概率明显降低。
基于东部地区某市的微观调查发现,东部地区劳动力流动缓解了主观感受下的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但对缓解主观感受下的相对贫困更显著。劳动力受教育程度、性别、年龄、务工经历、所从事行业等不同特征导致劳动力外出务工收入呈现差异化特征。其中,外出务工者在40岁时月收入达到峰值,构成了其与年龄二者间“倒U型”曲线的拐点;从事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讯业和批发零售业等务工者收入相对较高,而建筑业和制造业收入相对较低。
基于中部地区三市的微观调查发现,中部地区劳动力流动能够增加农村家庭收入,缓解家庭贫困,且劳动力流动规模越大,对农村家庭的增收减贫效应就越明显。在流入地的具体选择上,相较于省内流动,省外流动尤其是流向经济更为发达的省市务工,收入提升效应更为明显。
基于西部地区两市的微观调查发现,西部地区农村劳动力流动不仅可以缓解家庭当前的贫困,还有助于降低家庭未来发生贫困的概率,表明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减贫效应具有可持续性。与省内流动相比,省外流动给家庭带来的增收效应和减贫效应更强。
从劳动力流动对地区贫困影响的异质性来看,劳动力流动对减缓不同地区贫困均产生正向影响,但边际效应呈现差异化特征,中部地区的减贫效应优于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即中部地区劳动力流动的减贫效应最大,东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小。
从劳动力流动对城乡贫困影响的异质性来看,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研究发现,劳动力流动会显著降低城市贫困程度,同时导致农村贫困程度提高,且劳动力流动对贫困的影响具有空间外溢效应。

实现三者间的有机协同
从上述结论可以看出,无论是全国还是地区,劳动力流动均缓解了贫困,但从城乡二维空间来看,劳动力流动对城市贫困和农村贫困存在正负效应,进而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城乡深度融合发展或延缓了其时间表。因此,进行有效的政策设计,发挥劳动力流动的减贫和城乡融合发展效应,进而实现三者间的有机协同,显得尤为紧迫和重要。
第一,将劳务输出纳入扶贫工作的战略框架,并凸显其战略地位,这是弥补传统区域开发扶贫的不足、纠正扶贫政策方向偏差和扶贫对象漏出的需要。尽管劳动力流动自20世纪80年代业已开始,然而劳务输出并不能给地方政府带来直接的财政收入,进而导致其在扶贫中往往流于形式,未实现劳务输出与减贫两者间的激励相容。因政府扶贫开发资源只流向贫困区域与贫困县域,而非贫困县的贫困人口以及劳动力外流的贫困群体并未得到足够关注。因此,将劳务输出与缓解贫困摆在同样的战略高度尤为必要。
第二,强化对留守家庭人员的帮扶维度和保障力度,做好外流劳动力的后方保障,提升劳动力流动减贫的潜在质量和效率。有劳动力流动的家庭中,留守老人、留守儿童和无劳动能力者的比例较高构成了重要的家庭负担,这也是致贫的关键诱因,因此,这理应构成扶贫聚焦的重中之重。在进行扶贫和防范返贫的动态监测时,应着重关注存在劳动力流动情形下老年人比例高的家庭,特别是对于有重病、大病患者和残疾人的家庭,应提高动态监测等级和监测强度,做好“事前防范、事后帮扶”,与此同时,通过建立非营利性养老服务机构、农村留守儿童救助中心等,建构和创新农村留守人员关爱扶贫体系,为其提供保障机制。
第三,发挥城乡和区域协同效应,实现城乡和区域间的扶贫脱贫一体化,并辅之以户籍及其背后所附属的系列福利制度改革。具体来说,为预防与缓解劳动力流动所带来的“新二元贫困”问题以及扶贫政策在空间上的偏差,注重城乡和地区间的协同,城镇和发达地区可以在享受外来劳动力对自身飞跃式发展贡献的同时,承担相应的扶贫脱贫义务,并发挥对农村中西部地区的辐射效应与扩散效应。作为主要流出地的农村和欠发达地区,需要改变传统劳务经济的单一思路,整合劳动力、人才、资本、信息、技术和管理等多种要素和资源,避免出现劳动力和人才流失给自身带来的内生动力不足的问题,实现自身的超常规发展,通过内生式发展实现可持续和更高标准的减贫,进而推进城乡深度融合。
第四,建立健全贫困人口和贫困家庭动态数据库、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和福利体系以及以劳动力市场需求为导向的教育与培训体系等两大体系,确保对贫困人口在空间上的动态追踪,并实现贫困人口、家庭和贫困地区的内生式脱贫。劳动力流动往往导致贫困由农村向城市、由欠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的空间位移。为追踪和锁定扶贫对象,校正扶贫在对象上的偏差,需要挖掘互联网+和大数据间的双重叠加效应,建立健全的贫困人口和贫困家庭动态数据库,动态监测不同时期、不同阶段劳动力流动对贫困影响的变化情况与变化趋势,跟踪和锁定扶贫对象适时进行系统干预和综合治理,并建立与完善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和福利体系,既实现外流劳动力在就业、社保、子女教育等方面的全国信息互联,又保障其与本地居民在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等方面的均等化。与此同时,为变“输血式扶贫”为“内生式发展脱贫”,可以建立以劳动力市场需求为导向的教育与培训体系,提升贫困人口和家庭的人力资本以及贫困地区的教育投入,应对贫困与扶贫的长期性。

第五,中国的减贫战略未来需要转向更为复杂的相对贫困、多维贫困和预防贫困发生问题,着力解决城乡发展多方面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推进城乡融合发展。一方面,单一收入维度标准的绝对贫困解决之后,教育、健康、养老、就业、住房等其他多重维度的相对贫困,构成我国下一步扶贫工作的重中之重。另一方面,建立和完善劳动力和人才要素在城乡间的自由流动机制,为乡村振兴和城乡深度发展提供最关键的能动要素。目前,城乡和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以及走向共同富裕的最大短板仍然在农村,而农村发展的滞后很大程度上在于长期以来劳动力和人才要素的流失和短缺。因此,需要从根本上推进阻碍劳动力流动与城乡融合协同发展的户籍、就业、医疗、养老、工伤、公共服务等系列体制机制改革。具体需要由城市偏向转为农村偏向,引导劳动力在城乡间的双向自由流动,尤其推动城镇劳动力和人才向农村流动,在规模与结构上契合和匹配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发展的双重空间需求,实现劳动力流动、贫困缓解和城乡融合相互间的有机协同,扎实有效推进共同富裕。
[本文系江苏省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共同富裕目标下劳动力流动推进江苏城乡融合机制研究”(22ZDA001)的阶段性成果]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816期第2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拓展阅读
旅游导向下的劳动力回流,如何促进乡村振兴?| 社会科学报
万象 | 数字化转型:文明形态背后的动力密码离不开“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