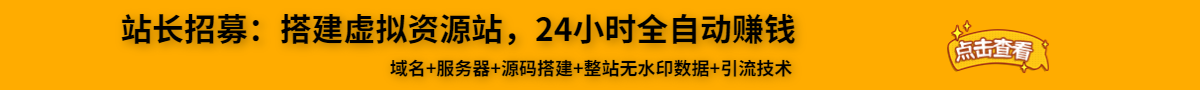#头条故事会#我生于1940年,出生地在湖北京山县宋河。宋河地处大洪山南麓,位于江汉平原北端,横跨大富水中游。清朝中叶,因得大富水河水运之便利,可与汉口通航,逐步发展为京山东北部山区香菇、板栗等土特产集市贸易场所。素有“小汉口“之美誉。四十年代,宋河为京山县第四区,有二三百户人家。
大约在1946年春天,宋河及周围的一些村庄的“开明绅士”共同出资聘请了一位晚清秀才,开办了一间小学,乡人通称为“私塾”。
私塾设在一大户人家的堂屋里。堂屋很大,摆了几张八仙桌,每桌三人,背朝先生的那方空着,其它三方各坐一人。坐凳是宽约四寸的长条凳,它有两用,一是坐人,二是刑具,即先生要打谁的屁股了,谁就自己将它扛到讲台前,趴到上面,请先生行杖。
那所谓杖,就是一块三尺多长二寸来宽的楠竹片。“行刑” 的厉害程度在于是否扒下裤子。是先生自己执杖,还是喊学生们来行杖。若是不脱裤子又喊学生行杖,就算轻刑,否则就重了。
先生高坐讲台上,面朝大门,背靠神龛。上有“天地君亲师之位”,下有“大成至圣先师孔子之位”的红底黑字的牌位,学生挨打之前要先向牌位鞠躬行礼。
上学的孩子不分大小,也不分年级,各读各的书。我从《三字经》开始学习,谓之发蒙。如我一般的孩子大约有十几个,比我们大些的学生大约七八个,他们读《论语》。
先生上课并无时限要求,各学生吃了早饭来上学。先生要吃午饭了就放学,下午也是如此。由于学生们读的书大都不同,上学有早有迟,所以就一个一个地教,真正是因材施教。
先生教书,并不先教我们识字的,而是让我们站在先生旁边,将书摊在桌上,先生念一句我们跟着读一句。先生认为你能记住多少,就念多少,有的人一天教三五句,有的人一天教十多句。
先生不念了,学生到各自的座位上去反覆背诵,直到自认为记熟了,就到讲台上去,把书递给先生,然后背给先生听。如果第一次背得不熟或者不流畅,就下去再读。直到将要放学时,先生叫你上台去背。如果再背不出,便只有挨竹板了。
打屁股是有定例的,每错一字打一板。打完就回家再读,次日早上跨进私熟大门就要背昨天的书,如果又背错了,就该扒下裤子打光屁股了。
有时先生一时兴起,背着手在各课桌间来回走动,看学生们是否认真念书。若发现谁没大声念诵,他会牢牢记住,等会儿你上去背书的时候,如若有错,那肯定扒下裤子挨打了。
除了背书就是写字。所谓教写字,就是“描红” ,即先生将你读的书用红墨(一种红色的石头磨出的水)写出十几个大字,称为“影本” ,自己在背熟以后,拿白纸蒙在上面一笔一画地描,也不管笔势、笔法、笔顺,每天描三张。
说来也怪,这样一字不识地背和写,居然不到半个月,我便把《三字经》背熟了,也写会了。即使先生在其中任意念一个上句,我便能接着背下去,直至先生叫停。这样,我在先生的心目中留下了一个聪明绝顶的印象,很受先生喜欢。因此我也常常被先生指定为“行刑” 的“刽子手”。在我的同龄人中,我本来就是个小头目,如今常常享有“行刑” 之权,就更加威风了,因为打轻打重,全看我手腕下多大的力。
我对于我拥有的权力只用过二次。
一次我用行杖之权救过我的好朋友王明鹏。有天下午,放学之前该背的书没有背熟,先生要他明早来背,这叫“寄打” 。“寄打” 比“兑现打” 厉害,是要扒下裤子打的。
晚饭后我们压根儿就忘了这回事,相约过河去找胡家畈的小孩打架,打完架已经很晚了,他不可能再去读书。于是,我们商量怎么躲过这一劫。
我讲出一个办法,明天我先到,他后到。他偷一个鸡蛋藏在身上,先生一叫我去打屁股时,他就赶紧扛起板凳上讲台,并不等先生叫扒裤子我就开打。
果然,先生上了我们的当。我一板子下去正正地打在鸡蛋上。蛋立刻就破了,蛋清蛋黄流了一屁股。我装着吓坏了的样子说道:“先生,把他的卵子打破了,怎么办?我不敢打了。”他跟着大叫大喊:“妈呀!打死我了!好疼哪!”他哭一声喊一声,又是眼泪又是鼻涕,一会儿就装着晕了过去。
这一下把先生也吓懵了,连连说道:“别打了,别打了,快把他送回家去”。我叫上另一个好友贾成刚,连板凳带人地抬着王明鹏到河里洗澡(如今称为游泳)、摸鱼去了。
直到下午我同贾成刚才回到学校。只见先生还在不停地搓着手来回踱步,很是担惊受怕的样子,见我们两个回来,忙问道:“王明鹏怎么样了?”我们说:“没事,先生,他家请了个过路的郎中给他缝好了,还敷了膏药,郎中说二三天就好。”先生又问道:“他家高堂怎么说?”我们不假思索地说道:“说怪他自己不好好念书,别的没说。”先生和我们都长长地嘘了一口气。这件事就这么糊里糊涂地混过去了。
另一次用权,更确切地说叫弄权。李勇刚只比我大几个月,可因为他父亲是我爷爷的亲弟弟,所以我该称他叔叔。他家比较有钱,但非常悭吝刻薄。李勇刚家以弟欺兄,以我爷爷老实,谋夺了家产并把我们一家赶出了李家的祖屋,弄得我爷爷和父亲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要不是邻居王家(我三爷爷儿媳的堂弟,我们称叔叔)好心收留,我们怕早已冻馁沟壑了。
我爷爷去世后父亲叫我去他家报丧。他家不仅不念手足之情来吊孝,反而由他妈(我们喊她四婆婆)把我轰出门,说:“死了就死了,大清早的跑来说这些不吉利的话做么事?”
我痛哭流涕跑回家,把她的话向父亲、姐姐和其他亲友学说一遍,听者无不痛恨。我更是咬牙切齿地大叫大喊:“老子总有一天要叫他认得我!”从此,我们两家的怨越结越深了。我那些“小的们” 也常常依我的吩咐,把李勇刚哄到没人的地方痛打一顿,为我出气。
这天他没背熟书,按例该打。先生叫我“行刑” ,我说:“先生,他是我叔,我打就是犯上。”先生说:“你真是个明理的学生,懂得长幼尊卑之意,难能可贵,难能可贵呀!但是,你行杖于他,是代夫子行事,原可大义灭亲的。你既然为难,我也不勉强于你,那就换一个人吧。”
今天书背得最好的除了我就数谭飞鹏、徐振华、陈文几个,先生指定了谭飞鹏。他是我的“小的们” 之一,朝我看了一眼,意思是“怎么打” ?我把眼神朝桌子底下看,手捏成拳头,做出使劲击打的样子。他立刻就明白我的意思:“朝死里打!”
他走上行杖处,问先生:“扒不扒裤子?”先生嗯了一声,恨恨地说:“叔叔不如侄子,还有何面目立于天地之间?给我扒了裤子打!”谭飞鹏毫不留情地动起手来,打得李勇刚杀猪般嚎叫,眼看那屁股肿了起来,青一块紫一块,慢慢血也浸出来了。
开打的时候,是先生在数数。我不知道会打多少下,想让李勇刚多挨几下,灵机一动,朝陈文、陈武兄弟俩和王明鹏递了个眼色,他们点头会意。先是陈文站起来大声说:“启禀先生,我要上茅房。”先生抽出一根木签递给他,这是准许离开讲堂的凭证,他拿着木签往外走。刚走出门,陈武、王明鹏也站起来禀报要求上茅房。按规矩只有一根签,要等第一个人回来了第二个人才能拿着木签出去。
现在刚出去了一个,又有两个人要去,先生就说话了,“你们一个一个地去,不得僭越!”原本就是要逗先生说话,因为他一说话就会忘了数数。谭飞鹏便趁机挥舞竹板使劲快打。
先生始终没弄清李勇刚究竟挨了多少板。等先生叫停的时候,李勇刚已经痛得哭不出声了。此后一连七八天都没来上学。回家后我对父亲说:“我今天报仇了!”父亲瞪了我一眼,什么也没说。大约过了一盏茶的功夫,父亲终于叹了一口气,说:“不打不成人哪,你们今天串起来打了他,说不定还是帮了他哩!”
在私塾里我也挨过一顿饱打,几乎打个半死,而且被人抬回家后又被父亲痛打一顿,以确认先生打得得当。
先生串讲四书五经时,讲到孔子周游列国经过卫国,游说国君时不得志,又耽搁了许多时间,于是去见了卫灵公的宠姬南子,想请她帮助說服卫灵公。南子是卫国第一大美女,在卫国是极有影响力的政治人物。孔子去见她,为学生所误会。子路就带头闹事,怀疑他被美女迷惑了。孔子赌咒发誓说不是这样的,“我怎会为美色所惑而忘了游说诸侯,推行仁政以礼治天下的志趣呢?男女授受相亲非礼也的道理,我会不知道吗? 若我是惑于美色,天打雷劈”!
这时我发问了,说道:“先生,孔夫子说的‘非礼’,或另有深意,既然不能授受相亲,何以孔子为其父母野合而生?何以孔夫子还有儿子呢?”先生不动声色地问道:“你怎知夫子为其父母野合而生?”我说:“我才看了司马迁先生的《史记》,上有孔子世家一篇, 里面写的明白.‘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俦于尼丘得孔子…….故因名曰丘,字仲尼,姓孔氏’,孔子若主张授受不亲,岂非忤逆父母,堪称不孝?”
我还想侃侃而谈,却被先生大声喝止,并立刻命人抬板凳扒裤子打屁股。先生大骂道:“侮慢圣人, 歪解经典,该重重责打”。先生还跪在孔子牌位前自掴耳光,泪流滿面,捶胸叹息道:“学生无能,教授无方,无颜面对先师。也是异数呀,异数! 我怎么就把一个聪明绝顶的弟子教成这个样子了呢?”
我趴在凳子上咬紧牙关,一声不吭,心里不停地咒骂道:“先生不讲理,先生不讲理,狗屁先生,狗屁先生!”也不知打了多少下,迷糊中有同学把我抬回了家。后来父亲去问了先生,向先生赔了罪,回家来又打了我两耳光和一顿屁股。
半年后办起了官学,私塾就停办了。直到上高中以后,书读得多了,我才明白这回挨打虽然很冤,但也应该。因为先生当年应试时便是以朱熹理学为范本的,而我的疑问确乎是歪解了朱氏《四书集注》,与先生所学相悖。为师道尊严故,揍我一顿,以儆效尤就实在应该了,谁教我读书不求甚解,自己撞到枪口上了呢?所以我不再埋怨先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