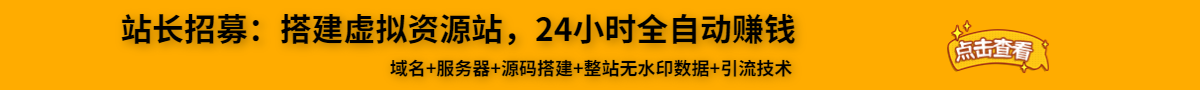蜀境/华西坝往事28
谭楷
华西坝的中国人若问起:“哪个是戴谦和?”答曰:“就是冬天喜欢穿‘抱鸡婆棉鞋’那个洋人。”
戴谦和(戚亚男提供)
戴谦和于1908年踏上中国的土地,是华西协合大学开办时的第一批教师,直到1948年退休回国,在成都生活了40年。
名如其人,真是“谦和”,中国人叫他“戴洋人”。据他的学生回忆:“先生非常简朴,衣着很不讲究。老穿一件过时的旧西装,袜子破了,皮鞋坏了,衣服烂了,修理补缀了再穿。他是西洋人中最不讲究的一位先生。冬天喜欢穿中式棉鞋,夏天爱穿黄色短裤,进城总是跑路。他说:‘跑路又经济,又可以运动一下身体’”。
戴谦和五次任理学院院长、数次兼任数理系系主任,曾培养了中国最优秀的天文学家李珩(晓舫)等一大批人才。最值得称道的是,他创建了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并担任了18年的馆长。博物馆集收藏、陈列、展览、研究、教育于一体,戴谦和承担了馆内全部事务。他支持了葛维汉发掘三星堆,真是奇功盖世。
落成于1926年的懋德堂,一楼为华西协合大学图书馆,二楼为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现为四川大学华西医学展览馆。(戚亚男摄于2011年)
谦谦君子
一生都在研读百科全书
熟知他的朋友说:“戴谦和不是考古学家,却是最热心的‘票友’。他的兴趣爱好实在太广泛了,一生都在研读百科全书。”
他喜欢仰望天空,关注风吹雨晴,每天详细记录成都天气,坚持了40年。他还请华西协合大学数理系毕业的张静如作助手,帮他作记录,以此研究太阳辐射和气温,了解哪些作物适合成都地区生长。华西坝的人士说:“要知道成都的天气如何,去问戴谦和吧。”
他还注目大地,从地理、地质到地下埋藏的文物,都怀有极大的兴趣。在广汉三星堆文物初露端倪之时,他就预言:“这个地区,将可能发现早期人类化石。”说这话25年后,在广汉以南,果然发现了“资阳人”头骨化石。
最早来华的传教士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化不太重视,更谈不上了解与尊重。莫尔思、戴谦和改变了方针,华西边疆研究学会将华西这块土地上的人文活动作为研究重点时,博物馆的独特与个性,就变得更加鲜明。
走在老街古巷,戴谦和的眼睛老盯着窗户?对,他就是在钻研中国的窗户。经30年努力,他竟收集了6000多种从秦汉到明清的窗格式样。他喜欢中国的窗户,在华西的博物馆和图书馆,凌空吊下的雕花窗户,成了独特而典雅的装饰,真令人叫绝。1937年牛津大学出版其所著《中国窗格图案》,1943年哈佛燕京学社再版。该书运用西方科学方法来研究中国传统建筑艺术,融科学与艺术为一体,是国际汉学界研究中国窗格图案的权威之作。
他曾邀请博物馆的同事到他家作客,同事们发现了几只毛色鲜亮的小鸟在小院里盘桓。再细看,在一片草坪的角落,有一只石头打制的圆盘,盘内有浅浅的清水,还有一碟鸟食。小鸟们飞来饮水,啄食,欢快地啼鸣着。戴谦和压低了嗓门,向同事介绍:“这是我家的常客,老朋友。”原来,戴夫人喜欢观察、拍摄鸟类,有了这鸟儿们戏水,饮水,啄食的好地方,给夫人创造了极佳的研究与拍摄机会。当时,戴谦和那一副得意,快乐劲儿,简直像个老顽童。
“野心勃勃”
华大博物馆要成当世一流
但是,在博物馆的建设方面,戴谦和不但不“谦和”,反而显得“野心勃勃”。
首先,他一提及大学办的博物馆,言必称“哈佛”:“现代大学如果没有一个好的博物馆,是不完善的。一些一流大学不仅拥有博物馆,而且还创办有几个博物馆,如哈佛大学拥有福格艺术博物馆、皮博迪博物馆、日耳曼博物馆、生物博物馆、植物博物馆。”
黄思礼说:“华西被公认是一个人种学家、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的天堂。华西边疆研究学会应积极参与葛维汉博士的博物馆活动,我们可以在物质方面协助他,建成一座名声在外的博物馆,是世界其它地方所不能超越的。”
戴谦和的好友、当时还在为美国国家博物馆收集标本的葛维汉,看到了博物馆的紧迫性与重要性:“这些文化遗产是非常丰富的,现在正濒临消亡过程中”。他呼吁传教士们“为博物馆作出贡献,在它们消亡之前收藏于博物馆”。他坚信“(华西协合大学的)博物馆有朝一日将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博物馆”。
四川大学博物馆馆藏的陶然士相片。 四川大学博物馆供图
1914年,华西协合大学仅有一个博物部,辅助戴谦和的是陶然士和叶长青。这两位传教士熟悉“藏彝走廊”,见多识广,眼光锐利,戴谦和如获天祐神助,不断施展吸入文物宝藏的“法力”。
在川大博物馆走廊墙上,有一张华西边疆研究学会1934-1935年度学术执行委员会的合影,居中一位大腹便便的学者,就是叶长青。他是长者、先行者,像一尊神,兀自站立在第一排正中,两边的学者都坐着。或许,从这张照片,让我们知道他的地位,他是边疆研究会唯一的一位荣誉会长。
慷慨解囊
叶长青捐出数百件史前石器
作为学者,叶长青精通汉语和藏语,甚至藏区内不同地方语。对于发韧于20世纪20年代的藏学研究,叶长青发表了大量有价值的藏学论著,无疑是民国时期藏学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他以坚毅的脚步行进在青藏高原东部横断山脉的“藏彝走廊”——有极高山峰、低海拔冰川、湍急河流、高寒草原和深切峡谷的金沙江、大渡河、雅砻江流域;以近于疯狂的热情研究贡嘎山,他努力绘制并用文字描述“藏东最高峰”。他除了研究佛教传入之前西藏流行的苯教和传入后藏传佛教的各个派别,还讨论藏区宗教的多样性。最难能可贵的是,“他没有以基督教神学作为价值判断的基点,将非基督教的宗教视为偶像崇拜或迷信、异端,而是将各个不同宗教视为不同的文化圈,相互之间存在交流与融合。”
叶长青有一种不达目的誓不休的深钻精神。他通过上层人士疏通关系并获得了尼庵主持允许,走进尼庵,作了实地考察。在《西藏的尼庵和觉姆》一文中,他描述了自己深深弯腰,钻进低矮狭窄“永远不可能让居住者感到舒适”的起居室,觉姆“睡觉时必须蜷缩着身体,或如佛像一样盘腿打坐,在任何情况下她们都不可能伸直身体”。叶长青第一次让世人知晓,觉姆就在这样的尼庵过着圣洁的修行生活。
从1907年开始,叶长青就在注意收集史前人类使用过的石器。戴谦和、葛维汉认为,叶长青是四川乃至华西史前石器的发现者。他将自己收藏的数百件史前石器悉数捐赠给博物馆,加上他帮助博物馆收购的石器。葛维汉评价说:“它们在任何博物馆,都会成为最好的中国石器时代的藏品。”
玻璃柜中的石锛、石斧,比广汉三星堆的文物早一千年至几千年。当年,古蜀先民凭着这些原始工具开天辟地,顽强生活。这些石器,又如同地标一样,将古蜀人的分布,迁徙路线指示得一清二楚。
卓越建树
陶然士致力研究四川古代史
徜徉在博物馆,从石器时代几步就跨越万年,走到汉代。汉砖、汉阙拓片、陪葬的陶制人物,让我们听到了两千年前的笑声。说书人在笑,杂耍人在笑,农妇在笑,家禽在笑。一座农家院内,有家禽,有猪和牛,与至今犹存的川西农家大院没有太大的差别。
走近了汉代的“农家乐”,陶俑都带着笑,有抿嘴微笑,有捧腹大笑,真是笑得丰富多彩。那时人们过着简朴、单纯的农耕生活,容易满足。再看现代人,整天忙忙碌碌,不时皱紧眉头,哪有这种天真的笑。可见,百倍的物质财富,并不能给人们带来百倍的欢乐。
陶然士和他的中国朋友。(陶然士家族收藏,吴达民 摄)
陶然士夫妇和第一个孩子玛丽,1912年。(陶然士家族提供,吴达民 摄)
除了叶长青,另一位帮助戴谦和的人就是内地会传教士陶然士,擅长用中文写作的考古学家。他为博物馆收购了5000件藏品,主要是汉代和羌族文物。1908年,他就在乐山发掘了一座崖墓,就像打通了一条时间隧洞——他到了东汉。陪葬的,几乎没有一样物品是当地老百姓认为是值钱的东西,全是大大小小的陶俑,人人,狗狗,马马。而从考古学家眼中,却看到了近两千年前东汉人鲜活的生活场景。
陶然士还是发现和考证称为四川“蛮子”遗址的第一个西方人,也是最早发现华西石棺葬陶器遗物的学者。他致力于四川古代历史研究,1916年成都华英书局出版了他的学术著作《成都早期历史:从周朝到蜀汉王朝的灭亡》。1922年翻译了《华阳国志》中有关蜀国的章节,并发表在《华西教会新闻》上,将古蜀文化介绍给西方读者。陶然士亦是羌族研究的先行者,其最重要的学术贡献是对羌族的宗教信仰作了较为全面系统的阐述,专著有《青衣羌——羌族的历史、习俗和宗教》、《羌族宗教的基本精神理念》等。因其在华西考古学和文化人类学方面的卓越建树,被当代民族学和人类学家李绍明视为中国人类学华西学派的主要人物之一。
【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欢迎向我们报料,一经采纳有费用酬谢。报料微信关注:ihxdsb,报料QQ:33864057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