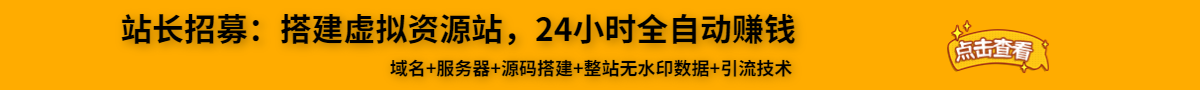内容提要:史载周武王克商后,设“三监”来管理商王畿地区,但何谓“三监”,如何管理?史书记载却颇为纷杂。《逸周书·作雒》说让武庚守商先王之祭祀,又将商王畿划为“东”、“殷”两部分,分别让管叔、蔡叔、霍叔管辖。而东汉班固《汉书·地理志》与郑玄《诗·邶鄘卫谱》均说将商王畿分为邶、鄘、卫三部分,让武庚与“三监”来管辖。但何谓“三监”,二书记载又有不同。
又,武王死后,武庚与“三监”发动叛乱,周成王平叛后,让康叔管理商王畿。但何年分封、如何分封,出土文献与史书记载亦多歧异。周初的沬司徒疑簋曰“令康侯啚(鄙)于卫”; 《逸周书·作雒》说成王让康叔管理“殷”,其子中旄父管理“东”; 《左传》定公四年说封康叔于“殷虚”; 《尚书大传》说“四年建侯卫”; 班固《汉书·地理志》说“尽以其地封弟康叔”; 而新近公布的清华简《系年》则谓“先建康叔于康丘,以侯殷之余民。卫人自康丘迁于淇卫“。
对于这些问题,从汉代至今,古今学者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本文通过考证清华简《系年》,认为《系年》所谓“先建康叔于康丘”指康叔分封在成王四年普遍分封诸侯之“先”,具体在成王二年; 并结合《汉书?地理志》等考证出康丘是康叔在邶建立都邑的地点,而邶即在殷墟。并认为,周武王在克商之后立武庚、设三监,主要是鉴于当时仍很强大的商人势力。“三监”具有军监性质,驻军地点是邶、鄘、卫三地。周成王二年“克殷”之后,将邶、鄘之民中的大部分迁到九里囚禁之,后又迁到洛邑。未迁走所余之殷民分为两部分:邶地之民分给康叔; 鄘地之民分给微子启,不久被迁到宋国。邶、鄘之民被迁后,成王将整个商王畿分给康叔管辖,具体分封的地点是康丘(即在殷墟)。由于地域辽阔,康叔与其子中旄父分而治之,分别管辖“殷(邶、鄘)”与“东(卫)”。成王三年践奄之后,康叔到周王朝任司寇,其所辖之民又从康丘迁到卫。殷墟的形成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周人的破坏,另一方面则是殷民的外迁。形成时间亦在周成王二年克殷之后。
一、问题的提出
商周王朝的交替是中国先秦时代非常重要的一段历史,然而周王朝的建立和巩固并非一帆风顺。周武王通过牧野一战虽然在时间上完成了商周交替,历史也进入史家所谓的西周时代。但是,从地理空间上讲,当时的商王畿仍然盘踞着以武庚为首的殷遗民,而且在商王畿以东,仍有徐、奄等与武庚关系非常密切之国。对这些地区的占领,实际上直到周成王时期才得以完成。成王通过“克殷”、“践奄”,占领商王畿以及徐、奄等地,又把盘踞于此的商遗民分而治之,一部分迁到洛邑集中管理,另外一部分则分给卫、宋等国。通过这些措施,成王才制伏了残余的殷商势力,巩固了周王朝。因此,《左传》定公四年说“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这是非常准确的。
实际上,关于成王如何巩固周王朝,传世文献与金文资料虽有较多记载,但相关记载不仅简略,在地理空间上也很含糊,导致史家对这一段重要历史的叙述颇为混乱。譬如,周武王克商以后,立纣王之子武庚禄父,让他守商先王之祭祀。《逸周书·作雒》说将商王畿划为“殷”与“东”两部分,而东汉班固《汉书·地理志》与郑玄《诗·邶邶卫谱》均说分为邶、鄘、卫三部分。那么,邶、鄘、卫与“殷”、“东”有何关系,具体地望在何处呢?
又,周成王平定三监叛乱后,《逸周书·作雒》说成王让康叔管理“殷”,其子中旄父管理“东”。《左传》定公四年说封康叔于“殷虚”。而周初青铜器沬司徒疑簋(《集成》4059)曰“令康侯啚(鄙)于卫”。[1]班固《汉书·地理志》说“尽以其地封弟康叔”。那么,“殷”、“东”、“卫”与“殷虚”的关系如何,康叔分封的具体情形又如何,这些记载之间又是什么关系呢?
实际上,对于以上很多问题,自汉代至今,学者争论不休,莫衷一是。[2]在这种情形下,只能希冀于新材料的发现。值得庆幸的是,二〇一一年公布的清华简《系年》亦有相关记载,给我们研究相关问题提供了新的契机。
据《系年》,周成王平叛后,把殷民迁到洛邑,然后开始分封诸侯; 在此之前,先把康叔封在“康丘”监管殷余民; 后来康叔所封之民从康丘迁徙到了淇卫。这是关于康叔分封较具体且特别重要的记载。关于卫分封的时间,《左传》等传世文献均载在周成王时期,宋代兴起了改经疑经之风,认为康叔分封在武王时期。[3]由《系年》来看,武王封卫说是不可信的。[4]又,《尚书大传》曰“四年建侯卫”,学者据此认为是周成王四年封卫; 实际上这里的“侯卫”即《尚书·酒诰》所载的“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之“侯”、“卫”,是诸侯的名称。因此,《尚书大传》“四年建侯卫”是指四年普遍分封诸侯(后文有详述)。而且《系年》明确记载是“先建”康叔,即康叔分封在普遍分封诸侯之“先”; 那么,具体在何时呢?另外,《系年》说康叔分封的地点在“康丘”,其具体位置又在何处?二〇一五年公布的清华伍《汤处于汤丘》有“汤丘”之名,有学者认为即康丘,那么,此汤丘、康丘与上引邶、鄘、卫和“殷”、“东”以及“殷虚”有何关系呢?对这些问题,学者也是见仁见智,争论颇多。[5]
实际上,关于邶、鄘、卫、“殷”、“东”、康丘、汤丘等地名的辨析,不仅是关于当时历史地理的考证,也关涉周初一些重大历史问题的厘清,比如周武王如何设三监,周成王如何平叛,平叛之后如何处置殷遗民、如何分封卫国等等。下面,结合新公布的清华简等资料,通过对上述地名的考证,希冀对周初一些重大历史问题的研究有所裨益。
一、周武王封武庚与设三监
周武王于甲子日早晨发动牧野之战克商,“厌旦于牧之野,鼓之而纣卒易乡(向),遂乘殷人而诛纣。盖杀者非周人,因殷人也。故无首虏之获,无蹈难之赏“(《荀子·儒效》)[6]。商纣之所以失败,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商人“纣卒易乡(向)”,司马迁亦载因“倒兵以战”(《史记·周本纪》),也就是说周人实际上没费多大气力灭商,这也产生了两方面后果:
一方面,商人的主要势力,尤其是其主力——“三百六十夫”——仍然存在,而这也成为周武王灭商后的心腹大患,以致令他夜不能寐。对此,《逸周书·度邑》曰:
王至于周,自□至于丘中,具明不寝。…… 叔旦亟奔即王。曰:“久忧劳,问周(曷)不寝?”…… (王)曰:“…… 维天建殷,厥征天民名三百六十夫。弗顾,亦不宾成,用戾于今。…… 我来所定天保,何寝能欲?”[7]
周武王之所以未能安寝,就是因为“厥征天民名三百六十夫。弗顾,亦不宾成,用戾于今“,《史记·周本纪》作”其登名民三百六十夫,不显亦不宾灭,以至今“。这“三百六十夫”,就是殷人的主力。[8]“用戾于今”、“以至今”,说明克商之后,殷人的主力仍在。
另一方面,牧野之战后,周人实际控制范围未能深入到殷旧境,尤其是东方地区。
《左传》成公十一年:“昔周克商,使诸侯抚封,(郑玄《礼记》注:”抚犹有也。“)苏忿生以温为司寇,与檀伯达封于河。” “温即今河南温县,檀在河南济源县,二者均在黄河北,且近于河,故曰”封于河“[9]。这说明周人控制了黄河北岸太行山东南的“河内”地区。
《左传》昭公九年载周景王使詹桓伯辞于晋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骀、芮、岐、毕,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东土也; 巴、濮、楚、邓,吾南土也; 肃慎、燕、亳,吾北土也。“实际上,武王克商后,蒲姑(今山东博兴县东南十五里)、商奄(今山东曲阜县东)等地仍盘踞着殷人势力,周人实际控制的范围根本未达到如此广阔之区域。
王国维说:“武王克纣之后,立武庚置三监而去,未能抚有东土也。逮武庚之乱,始以兵力平定东方。“[10]吕思勉说得更具体,他说武王克商后,”此时周之兵力,实未踰殷之旧境。《史记》述周初封国(指《史记》所载封周公于鲁等事——引者按),盖杂后来之事言之,非当时实锈也。…… 盖管为东方重镇,周初兵力所极。纣地既未能有,仍以封其子武庚; 淮夷、徐戎等,又为力所未及; 则武王时,周之王业,所成者亦仅矣。故殷、周之兴亡,实至武庚败亡而后定“[11]。这种论断是非常正确的。也就是说,牧野之战后,周人控制的实际范围最东部应该就在管地(今河南郑州市西北管城),而其以东、以北区域实际上仍为商人所控制。
总之,在牧野之战后,商人的主力所谓“三百六十夫”仍然存在,其旧地的大部分区域仍然盘踞着商人势力,尤其以殷贵族基层“士”一级的人数众多,很难统治,[12]面对这种局面,周武王采取了两方面措施:
一方面,不得不对殷遗民加以安抚笼络,封纣王之子武庚作为殷后以续祭祀。《逸周书·作雒》曰:“武王克殷,乃立王子禄父,俾守商祀。“孔晁注:”封以郐,祭成汤。“[13]《史记·殷本纪》曰:”(周武王)封纣子武庚禄父,以续殷祀,令修行盘庚之政。殷民大说(悦)。“《史记·卫世家》说”复以殷余民封纣子武庚禄父,比诸侯,以奉其先祀勿絶。“可见,周武王立武庚的主要目的表面上是为了让其继续祭祀殷先王,实际上是笼络人心。
另一方面,武王又担心以武庚为首的殷遗民,所以不得不对其采取防范措施,让管叔、蔡叔、霍叔监视之。《史记·周本纪》载当时的情形是“武王为殷初定未集,乃使其弟管叔鲜、蔡叔度相禄父治殷”。《史记·卫世家》说的更明确:“武王已克殷纣,复以殷余民封纣子武庚禄父,比诸侯,以奉其先祀勿絶。为武庚未集,恐其有贼心。“也就是说,周武王克商后,”殷初定未集“主要指以武庚为首的殷遗民集团,而且周武王已经”恐其(指武庚——引者按)有贼心“。既然如此“恐”,为何还要立武庚,根本原因是周武王克商后,殷商残余势力依然非常强大。蒙文通说:“以三监镇殷墟,……《王制》言:’天子使其大夫为三监,监于方伯之国。’岂彼时殷势尚盛,故以武庚为方伯耶。“[14]所言极是。
《尚书·大诰》中周人自称为“小邦周”,而在《召诰》、《顾命》中称殷为“大邦殷”,周人能够通过牧野一战取得小国对于大国的胜利,已属不易; 而以小国统治大国,就更加不易。因此,面对周人一时还不能镇服的以武庚为首的殷遗民,以及无法全面直接统治的殷王畿旧地,周武王采取了封武庚、设三监的措施。
班固《汉书·地理志》:“河内本殷之旧都,周既灭殷,分其畿内为三国,…… 郐(即邶,后同——引者按),以封纣子武庚; 庸(即鄘,后同——引者按),管叔尹之; 卫,蔡叔尹之:以监殷民,谓之三监。”
郑玄《诗·邶鄘卫谱》:“邶、鄘、卫者,商纣畿内方千里之地。…… 周武王伐纣,以其京师封纣子武庚为殷后。庶殷顽民,被纣化日久,未可以建诸侯,乃三分其地,置三监,使管叔、蔡叔、霍叔尹而教之。自纣城而北谓之邶,南谓之鄘,东谓之卫。”[15]
以上两种说法有差异:班固说三监指武庚、管叔、蔡叔,而郑玄说是管叔、蔡叔、霍叔,那么究竟孰是孰非?对此,清代学者陈启源说:
一、引言
三监是管、蔡、霍,武庚不在三监之中。《汉记》三监有武庚无霍叔,则管、蔡所监亦不足据信。故郑不指言之,斯言良是!然源谓《汉记》非误,但述之未详耳!
宋章氏《山堂考索》论武王之封武庚,知其必叛,故立三监使治其国,而纳其贡税,一如舜之封象。此虽臆说,而事势或有然。殷既三分三叔,当分治之。《汉记》既言管、蔡监卫、鄘,则霍叔监邶不言可知; 又与武庚同国,故略而弗着,非谓武庚亦一监也。《史记正义》引《帝王世纪》以为管叔监卫、蔡叔监鄘、霍叔监邶,此言管、蔡所监,虽与《汉记》异,而言霍之监邶,足补《汉记》之未及也。《周书·作雒解》孔晁注云:“霍叔相禄父。“言”相“则必立于其朝,其监邶信矣!盖二叔监之于外,以戢其羽翼; 霍叔监之于内,以定其腹心。当日制殷方略,想应如此。
厥后周公诛三监,霍叔罪独轻者,良以谋叛之事,武庚主之,霍叔与之同居,意虽不欲势难立异。非若二叔在外,可以进退惟我也。原设监之意,本使之制殷。但武庚故君之子,又据旧都,臣民所心附。观其惎间周室,俾骨肉相雠,易于反掌,为人必多智数。霍叔才非其敌,堕其术中,遂反为所制耳!故《周书·多士》止数管、蔡、商、奄为四国,《破斧诗》四国毛亦以为管、蔡、商、奄,皆不及霍,则霍叔与武庚同在邶,固无可疑者。[16]
陈启源认为三监指管叔、蔡叔、霍叔,武庚则是被监之对象。武庚与霍叔同在邶,霍叔立于武庚朝中,监视武庚; 而管叔、蔡叔在卫、鄘,从外部监视武庚。这些看法是正确的。需要补充的是,武庚实际所封是整个商王畿,领有邶、鄘、卫三地; 武庚具体居地在邶。那么,邶、鄘、卫的性质又如何呢?
上文已述,周武王时根本没有能力把武庚所盘踞的商王畿划分为三国,正如郑玄所说当时“庶殷顽民,被纣化日久,未可以建诸侯”,于是三分其地成邶、鄘、卫,分别让霍叔、蔡叔、管叔“尹而教之”。“尹”,《说文·又部》:“尹,治也。从又丿,握事者也。“段注:”又为握,丿为事。“[17]故主管其事曰”尹“。这说明三监之设实际上是一种主管事的官职之名称,并非诸侯; 故邶、鄘、卫也就不是诸侯国。
清代学者朱鹤龄说:“武王既克殷,其封武庚必以大国。又虑武庚不靖,乃使三叔为之监。监者,监而治之,盖以殷之畿内渐纣化日久,未可建国,且使三人为之监领。“[18]”监领“者,监督主管的一种官职。孙作云认为,所谓邶、鄘、卫三国实际上不是国名,而是驻军地点名,三监就是三个驻军地点的军监[19]。李民也说,邶、鄘、卫是周人将商王畿及其周围分成三片,类似后世的三个军分区,邶、鄘、卫都驻有周人的军队,当时周人兵力不足以遍布各地,而由其驻军点藉以管辖所“监”之地[20]。笔者同意上述说法。
邶、鄘、卫是三个驻军点,由这三个驻军点所辐射的面就是所监之地。由于驻扎军队、人员众多,故此三个驻军点又具有都邑的性质[21]。东汉许慎《说文?邑部》:“邶,故商邑,自河内朝歌以北是也”[22],则邶是邑名; 又清华简《系年》第三章曰:“周武王既克殷,乃设三监于殷。武王陟,商邑兴反“[23],笔者认为”商邑“具体即指三监所辖之地,故邶、鄘、卫亦均为邑名。因此邶、鄘、卫既是周人的驻军点,又具有邑的性质。
邶、鄘、卫是三监驻军的三个都邑名称,周人于此驻军,对盘踞于此的殷人只起到一种震慑作用,以三监为代表的周人势力仍未深入商王畿内部。周人既然选择邶、鄘、卫驻军,此必为战略要地。邶既然为武庚所居,《逸周书·作雒》说武庚是“守商祀”,此地必为商人宗庙所在。周人派霍叔驻军于此,处于武庚腹心,此监于内者。卫地为管叔所监,位于商王畿以东,直接扼守商王畿与东方的交通,《逸周书·大匡》第三十七:“惟十有三祀,王在管,管叔自作殷之监。东隅之侯咸受赐于王,王乃旅之,以上东隅。“鄘地为蔡叔所驻军,与管叔所监之卫形成犄角之势[24]。
综上可见,周武王克商以后,实际上把整个殷王畿封给了武庚,但名义上的主要目的是让其继续商先王之祭祀,居于商王宗庙所在之邶。周武王为了防范他,又选择了商王畿的三个重要地点驻军,邶为武庚居地,派霍叔监之。卫为商王畿通往东方的门户,管叔监之。鄘则蔡叔监之,与卫形成了犄角之势。那么,邶、鄘、卫的具体地望在何处?又,《逸周书·作雒》载武王将商王畿分为“殷”、“东”,让蔡叔、霍叔管理“殷”,让管叔管理“东”,那么“殷”、“东”与邶、鄘、卫的关系又如何?下面对此考述之。
二、“殷”、“东”与邶、鄘、卫的关系及其地望
“殷”、“东”与邶、鄘、卫的区分与方位,古籍记载如下:
(1)《逸周书?作雒》:“武王克殷,乃立王子禄父,俾守商祀。建管叔于东,建蔡叔、霍叔于殷,俾监殷臣。“孔晁注:”封以郐,祭成汤。’东’谓卫,’殷’,鄘。“孙诒让说:”孔意盖以武庚所封者为鄁,管叔所治者为卫,蔡叔所治者为鄘,故云东谓卫(句),殷鄘(句)。不及’郐’者,上注已以’封郖’释’俾守商祀’句,故不复举也。又别释之云霍叔相禄父者,明正文虽以霍叔与蔡叔同建于殷,而治鄘者实止蔡叔一人,霍叔自与武庚同居鄁,鄁亦得为殷也。此孔分别诂释之意。”[25]
据此,则“殷”包括邶、鄘,而“东”则包括卫,曰“东”者,说明在“殷”之东。
(2)东汉班固《汉书·地理志》:“河内本殷之旧都,周既灭殷,分其畿内为三国,《诗·风》邶、庸(鄘)、卫国是也。郖(邶),以封纣子武庚; 庸(鄘),管叔尹之; 卫,蔡叔尹之:以监殷民,谓之三监。“颜师古注:”自纣城而北谓之邶,南谓之庸,东谓之卫。”[26]
(3)东汉郑玄《诗·邶鄘卫谱》:“邶、鄘、卫者,商纣畿内方千里之地。…… 周武王伐纣,以其京师封纣子武庚为殷后。庶殷顽民被纣化日久,未可以建诸侯,乃三分其地,置三监,使管叔、蔡叔、霍叔尹而教之。自纣城而北谓之邶,南谓之鄘,东谓之卫。“孔颖达疏:”…… 在纣都朝歌……。”[27]
可知郑玄所谓的纣都、纣城指朝歌。
(4)西晋皇甫谧《帝王世纪》:“自殷都以东为卫,管叔监之; 殷都以西为鄘,蔡叔监之; 殷都以北为邶,霍叔监之:是为三监。“(《史记·周本纪》正义引)[28]
要弄清“殷”、“东”与邶、鄘、卫的关系及其地望,首先须确认两个问题:第一,邶、鄘、卫是三监的军事据点,而非三个封国。第二,邶、鄘、卫以及“殷”、“东”方位的确定,是以朝歌为中心点区分方位,还是一种相对的位置?第一个问题前面已经说明,以下着重谈第二个问题。
根据上引文献来看,“邶”、“东”之称应该是因在北、在东而得名,那么,这个方位确定的参照物是什么?根据较早的文献《逸周书·作雒》、《汉书·地理志》来看,这个参照物可能是一种相对位置,比如邶、东应是位于商王畿以北、以东而得名。但东汉郑玄另立新说,他将武庚安置在“京师”“纣城”——实际上就是朝歌,然后以朝歌为中心点,区分北、南、东。这种看法影响了西晋皇甫谧、唐代颜师古以及后代很多学者。实际上,郑玄的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
郑玄之所以以朝歌为中心点,根据有二:一是认为朝歌是“纣城”、“京师”; 二是认为武庚即封在朝歌。但是,这两个根据都不能成立。首先,朝歌不是纣都“京师”,《古本竹书纪年》载:“自盘庚徙殷,至纣之灭,七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纣时稍大其邑,南距朝歌,北据邯郸及沙丘,皆为离宫别馆。“(《史记·殷本纪》正义转引《括地志》)[29]。可见,朝歌只是纣的“离宫别馆”,真正的都城在“殷”,即今安阳殷墟。其次,武庚封在邶而不在朝歌。《逸周书·作雒》未明确武庚所封地,东汉班固《汉书·地理志》说武庚封在邶,后代学者多从班固之说,如清代学者陈奂说:“邶,商邑名,在商都之北。武王封武庚为商后,其国不袭纣之故都,而徙于国北之邶邑。朝歌,纣故都也。“[30]顾颉刚说:”(郑玄说)武庚只封于纣都,在这京都的城圈子以外完全没有他的地方:这和《史记》、《汉书》之说均大不合“,所以”郑玄独谓武庚仅封纣城,不合事实“。[31]
笔者认为,“邶”、“东”等方位的确定,不是以朝歌为中心点,而是一种相对位置,也就是“邶”是因为在商王畿北部,“东”则是由于在其东部。
明确以上两点,下面再来考察邶、鄘、卫的地望。
关于邶、鄘、卫三地,古代学者多认为在商畿内。《汉书·地理志》:“河内本殷之旧都,周既灭殷,分其畿内为三国,《诗?风》邶、庸、卫国是也。“郑玄《诗?邶鄘卫谱》曰:”邶、鄘、卫者,殷纣畿内地名,属古冀州。自纣城而北曰邶,南曰鄘,东曰卫。“以上说法均认为邶、鄘、卫在商畿内,这种观点也为后世学者所遵循。
1890年,河北涞水张家洼曾发现邶伯器,王国维据此另辟新说,认为邶即是燕,其曰:
彝器中多北伯、北子器,不知出于何所。光绪庚寅直隶涞水县张家洼又出北伯器数种,余所见拓本有鼎一、卣一,鼎文云:“北伯作鼎”,卣文云:“北伯作宝尊彝”,北盖古之邶国也。自来说邶国者,虽以为在殷之北,然皆于朝歌左右求之。今则殷之故虚得于洹水,大且、大父、大兄三戈出于易州,则邶之故地自不得不更于其北求之。余谓邶即燕、鄘即鲁也。邶之为燕,可以北伯诸器出土之地证之。邶既远在殷北,则鄘亦不当求诸殷之境内,余谓鄘与奄声相近,…… 奄地在鲁。[32]
王国维根据在今河北涞水县所出北伯器,而涞水实际上属于燕,所以王氏认为邶即是燕。同样,“鄘”也不在商畿内,其与“奄”音近,应为鲁。实际上在王氏之前,清代学者许印林、方濬益早有此说[33]。陈梦家也说邶国“在今易水、涞水流域”[34]。
但是,后来得知,邶伯器不仅发现于河北涞水,1961年在湖北江陵发现一批西周早期铜器,其中七件有铭文,曰:“北子。……“(北子鼎,《集成》1719),”翏作北子柞簋……“(翏簋,《集成》3993)等[35]。郭沫若认为此北子即邶、鄘、卫之邶,北子器为何在湖北江陵出现?郭沫若认为其可能经过曲折过程,为楚国所俘获[36]。虽然学者对北子之器是否属于邶国有不同看法[37],但从中可以看到,纯粹以出土地点来认定邶在河北涞水实际上是不可靠的; 况且光绪年间河北涞水的“北伯”器并非科学发掘,不能证明这些铜器即出土于北伯墓中,还有可能是远距离迁徙所致。[38]
如此看来,河北涞水的邶伯器是否真的就反映出周初邶国之所在,这是非常值得怀疑的; 所以传统学者所认为的邶、鄘、卫在商畿内的说法,尚无足够的理由予以推翻。
最近公布的清华简《系年》第三章说:“周武王既克殷,乃设三监于殷。武王陟,商邑兴反,杀三监而立彔子耿。成王屎伐商邑,杀彔子耿。“[39]可见”三监“之设确实在殷; 后来三监反,《系年》说“商邑”反。何谓“商邑”?《诗·商颂·殷武》:“商邑翼翼,四方之极。“朱熹注:”商邑,王都也。“[40]《白虎通?京师篇》:”夏曰夏邑,殷曰商邑,周曰京师“,[41]可见”商邑“实际上就是殷都,这说明三监之设就在商王畿内。
既然“三监”所设立的邶、鄘、卫在商畿之内,所以应在商畿内寻找。
(一)邶的地望
关于“邶”,文献作如下记载:
(1)东汉许慎《说文?邑部》:“邶,故商邑,自河内朝歌以北是也。”[42]
(2)东汉郑玄《诗?邶鄘卫谱》:“自纣城而北谓之邶。”
(3)西晋皇甫谧《帝王世纪》:“殷都以北为邶。“(《史记·周本纪》正义引)
(4)南朝宋范晔《后汉书?郡国志》:河内郡朝歌,“北有邶国”。
可见,“邶”从“北”,就是因在北得名。皇甫谧说是在“殷都”以北,实际上他是把朝歌作为“殷都”,但这是有问题的,前文已述“邶”的得名是由于在商王畿北部。
既然邶在商王畿北部,那么其具体位置在何处呢?对此,对此,主要有以下几种说法:
一是认为在今河北南部,如于省吾认为邶指殷都(安阳)以北,在今河北南部。[43]
二是认为邶即庇,在今河北南部以至北部一带,杨筠如曰:“疑’庇’即邶、鄘、卫之邶,吉金文止作’北’。“[44]顾颉刚、杨宽以此为据,认为”邶“即”庇“,顾先生认为在今河北南部到河北北部,[45]杨先生认为在今河北邢台。[46]
三是以“邶”作“郐”为据,认为邶因背朝黄河得名,在今河南汤阴以南、浚县、滑县和淇县一带。[47]
四是以后世的“北城”、“鄁水”等推断在纣城(淇县)东北、殷都(安阳)东南。[48]
五是认为在今安阳殷墟一带。清人雷学淇说:“经传凡言武庚之国皆谓之殷,则武庚实封在于邺南之殷可知。此时商之宗庙在殷,故《周书》曰’俾守商祀’。“[49]韦心滢也以武庚守商祀以及考古上发现商后期的宗庙在安阳小屯为据,认为邶的范围应在安阳及其周围区域,最北或可达漳河流域。[50]
笔者认为最后一种说法近似,且邶就在殷墟,今河南安阳一带。此地可能就是武庚的驻扎地,霍叔的驻军点也在此。
根据考古发现,殷墟遗址群分布于河南安阳西北郊的洹河两岸,总面积约30平方公里。其中有两个中心点:洹河南以小屯、花园庄为中心的宫殿宗庙区和洹河北以侯家庄、武官村为中心的王陵区,两处地势较高。在洹河两岸,分布着其它的居住址及手工业作坊,族墓地分布在居住区附近及外围地区。
笔者之所以认为邶在殷墟,主要基于以下理由:
第一、时代符合。对于殷墟文化的分期,一般分为四期,其中第四期传统上普遍认为相当于帝乙、帝辛时期。[51]后来考古学家通过对殷墟文化第四期最末阶段(IV5)[52]遗存的分析,发现这些文化尽管文化属性可归于商文化,但其年代已进入西周初年,典型者如殷墟西区M1713,考古工作者认为该墓的下葬年代在帝辛七年至周公东征胜利之前,可能葬于“武庚监国”时期。[53]
第二、地域符合。文献记载邶在商王畿北部,朝歌以北,与殷墟位置正合。武庚封在朝歌以北的殷墟,而邶是霍叔的一个军事据点,也在殷墟。
第三、与武庚禄父“俾守商祀”的记载相合。传世文献记载,武王封禄父在邶,其中一个目的即是“俾守商祀”。《逸周书?作雒》:“武王克殷,乃立王子禄父,俾守商祀。“《史记·卫世家》:”武王已克殷纣,复以殷余民封纣子武庚禄父,比诸侯,以奉其先祀勿絶。“《史记·宋世家》:”武王封纣子武庚禄父以续殷祀。“既然武庚封于此是”守商祀“,此地必有宗庙等祭祀场所或遗迹,而这些在殷墟正好都有发现。
殷墟遗址洹河南岸的小屯东北地是殷王朝的宫殿宗庙区。其中乙组基址的乙七、乙八可能就是宗庙性建筑; 丙组基址的丙三、丙四、丙五、丙六可能为祭坛一类的建筑,与乙组宗庙遗址有密切关系。[54]在宗庙宫殿区分布着很多祭祀遗存,其中祭祀遗存最丰富的是乙七基址,东西长约44米,南北宽25米以上,乙七基址南部的葬坑有134座。[55]学者推断乙七基址为晚商时期较早阶段的宗庙,其祭祀对象为商王的列祖列宗。[56]丙二大概为住宅,但分布于其周围的小葬坑,有可能是祭祀宗庙中先公先王的牺牲时所留之遗存。[57]1989年发掘的丁组基址,主殿前面有祭祀坑,埋葬人牲,考古学家推断大概是用于祭祀的宗庙性建筑[58]。
在洹河以北的王陵区,迄今共发掘大墓14座,祭祀坑近1500座。在安阳西北郊的武官村侯家庄北,大墓分东西两区,西区有四条墓道的大墓7座(HPKM1001、M1002、M1003、M1004、M1217、M1500、M1550),一条墓道的大墓1座(78AHBM1),以及未完成的大墓1座(HPKM1567)。东区有四条墓道的大墓1座(HPKM1400)。杨锡璋认为,M1001、M1550、M1400属于殷墟二期,M1004、M1002、M1500、M1217属于殷墟三期,M1003属于殷墟四期,它们是从武丁到帝乙八位商王的陵墓[59]。因为殷墟第四期相当于帝乙帝辛时期,而M1003是帝乙的陵墓,而M1567晚于M1003,所以学者推断M1567可能是为帝辛而造的陵墓[60]。
在王陵区的东区大墓旁,分布着大量的祭祀坑,总数在2500座以上,现已清理1487座(该统计数字包括少数陪葬墓),主要集中在王陵区东区的西、南和西南部。[61]学者认为,王陵东区是商王室用于祭祀其先祖的一个公共祭祀场地[62]。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位于殷墟东南部、高楼庄村北后冈南坡的殷代圆形墓葬坑(59AHGH10,简化为HGH10)口径2.2、底径2.3、深2.8米,坑内共埋葬约属73个个体的人骨(大多为青壮年),随葬铜器10件、陶器32件、玉器5件、兽骨象牙器13件、贝718枚、谷物、丝麻纺织品等。葬坑所出铜器中,礼器有鼎、卣爵各1件; 工具和武器有刀(1件)、戈(2件)、镞(1件),另还有装饰品铜铃和铜泡各1件,璜形器1件[63]。葬坑所出戍嗣子鼎(《集成》2708)曰:“丙午,王赏戍嗣子贝廿朋,在宗,用作父癸宝。惟王大室,在九月。犬鱼。”
关于赐葬坑的性质,以前有祭祀坑和殉葬坑两种说法,后来杜金鹏从坑形、葬品等各方面否定了这两种说法,他认为此葬坑虽可归入墓葬之列,但非正常墓葬,而是特殊的埋葬遗存; 葬坑年代大约为殷末或殷周之际,他并结合牧野之战这一背景,认为这些死者是牧野之战的殉国者; 之所以说是“非正常埋葬”,是因为死者“因是(殷商——引者按)高级官员得以享受较多随葬品; 情况紧急不容全礼,因而匆匆埋葬,致使墓穴简陋,无有棺椁,尸骨凌乱“。[64]我们同意墓葬年代应在殷周之际,葬坑为特殊的埋葬遗存,死者是牧野之战殉国者的说法。但埋藏这些殉国者的人是谁?为何如此“匆匆埋葬”,杜氏所言不详,或可补充如下:笔者以为,埋藏死者之人应是以盘庚为首的殷遗民; 又因这些死者是牧野之战死的,作为牧野之战的失败者,他们不能明目张胆地、用全礼埋葬这些死难者,所以只能匆匆埋葬这些人。关于这些死难者的身份,裘锡圭认为“戍”是殷王朝的一种官职,葬坑里的青年男子就是铜鼎的所有者戍嗣子所统领的一队戍卒。[65]结合葬坑中的出土兵器以及牧野之战的背景,裘说可从。这些死难者可能是牧野之战中商人的一支戍守军队,其长官正是戍嗣子。
总之,根据各项数据分析,邶地就在殷墟,在今河南安阳。
(二)卫的地望
关于卫的地望,传世文献主要有如下说法:
第一、卫在朝歌之东。如东汉郑玄《诗·邶鄘卫谱》:“(纣城之)东谓之卫。“晋代孔晁《逸周书注》:”东谓衞。“晋代皇甫谧《帝王世纪》:”殷都以东为卫,管叔监之。“唐代颜师古《汉书注》:”(自纣城而)东谓之衞。”
第二、卫在朝歌之南。如清代魏源《诗古微·邶鄘卫义例篇上》:“自都城而南谓之卫。”[66]
第三、卫即朝歌。如清代陈奂《诗毛氏传疏》:“卫即朝歌。”[67]
以上三种说法中,第二种说法没有根据,学者甚少从之。以下主要分析第一种和第三种说法。
卫在商末已经存在,唐兰认为其为接近商都的一个国[68]。《逸周书?世俘解》载周武王克殷后,就立即攻占商的其他城邑,其中一个就叫“卫”。《逸周书·世俘解》:“甲申,百弇以虎贲誓,命伐卫,告以馘俘。“潘振曰:”卫,邑名,在朝歌之东。“陈逢衡曰:”以虎贲者,卫强于诸邑也。“[69]可见,卫实际上是朝歌以东的一个比较重要的邑,守卫力量非常强,所以周武王以虎贲之士攻伐。《逸周书·作雒》载周成王平定武庚叛乱,“临卫政(征)殷”。“殷”与“东”相对,所以“卫”就是“东”,其得名是由于在商王畿之东部。这说明第一种说法是有根据的。
又,《尚书·酒诰》载康叔封于妹邦,“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伪《孔传》:”妹,地名,纣所都朝歌以北是。“[70]”妹“地又称”妹土“(《酒诰》)、”沬之乡“(《诗?鄘风?桑中》)。“妹”地又见于金文。周初青铜器沬司徒疑簋载“王来伐商邑,诞令康侯啚(鄙)于卫,沬司徒疑眔啚(鄙),作厥考尊彝”(《集成》4059)。沬,即上引《酒诰》的“妹邦”。“眔”,张桂光证诸卜辞认为当取“一起”、“参与”之义。[71]成王令康侯(即康叔)“鄙于卫”,而妹司徒也一起参与,这说明妹属于“卫”。《系年》第四章:“卫人自康丘迁于淇卫。“整理者注:”即在淇水流域的朝歌,今河南淇县。“[72]以上文献都证明朝歌属于卫。可见,第三种说法也是有根据的。
实际上,第一种和第三种说法并不矛盾,笔者认为,卫就在商王畿以东,也包括朝歌。卫虽然也是管叔驻军之处,但在商末就存在,这说明卫不仅仅是一个驻军点,实际上包括一个较大的地理范围。那么其地望在何处呢?
有学者认为卫可能是后世的卫县。《括地志》:“纣都朝歌在卫州东北七十三里朝歌故城是也。“”朝歌故城在卫县西二十三里,卫州东北七十二里,谓之殷虚“。[73]《元和郡县图志?河北道》卫州条下:“卫县,本汉朝歌县,属河内郡。…… 大业三年,改朝歌为卫县,属汲郡。“但又说该县有”朝歌故城,在(卫)县西二十一里。殷之故都也“[74]。高士奇《春秋地名考略》卷七引杜佑曰:“卫县西二十五里有古朝歌城。“又引刘昫曰:”纣所都朝歌在(卫)县西。“[75]《大清一统志?河南卫辉府》”古迹条“曰:”卫县故城在濬(浚)县西南五十里,…… 今为卫县集。“[76]卫县集今又称卫贤集,位于今河南省浚县西南约25公里,西据朝歌镇即今淇县约10公里。[77]1932—1933年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和地方联合组成的河南古迹研究会在位于河南浚县西南隅的辛村进行发掘,整理者认为大致是西周时代到东周初年卫国贵族的埋葬地,在墓中出土的甲泡有铭曰“卫昜”,证明其确实是卫国墓地。[78]孙华认为辛村墓地“很可能开始于西周早期的卫国始封以后”。[79]2016年3月至10月,考古工作者又在河南淇县杨晋庄发现西周卫国墓群,墓葬时代最早可至西周早期偏早。[80]考古遗址进一步证实了卫应在河南浚县、淇县。可见,卫实际上包括今河南浚县、淇县等地域,由于位于商王畿以东,故《逸周书·作雒》又称“东”。
(三)鄘的地望
关于鄘的地望,有纣城西、南、东三说:持西说者如西晋时皇甫谧《帝王世纪》:“殷都以西为鄘,蔡叔监之”(《史记·周本纪》正义引); “东汉服虔、三国王肃也说鄘在”纣都之西“(《诗·邶鄘卫谱》正义引)[81]。持南说者如颜师古《汉书注》:“(自纣城而)南为庸(鄘)。“持东说者如陈奂《诗毛氏传疏》:”庸(鄘),在朝歌东…… 管叔尹。“[82]刘师培把《汉书》与《逸周书》的三监之说作比较,认为武庚别封在邶,蔡叔封于卫,管叔所封的鄘即是《逸周书》所说的”东“,而《逸周书》所说的”殷“应包括邶和卫。[83]
除以上诸说外,王国维在《北伯鼎跋》说“鄘即奄,后为鲁,封伯禽。“上文分析了邶、鄘、卫实际上都在商畿之内,而王说主要依据声韵通假之理但别无其他坚实依据,不可从。卫在东说有考古遗迹可证。所以鄘的地望只可能在商王畿西部或南部。《通典》“卫州新乡县”条曰“西南三十二里有鄘城,即鄘国”[84]。《太平寰宇记》亦曰:汲县有“鄘城,在今县东北十三里”[85]。古鄘城大概在今河南新乡、汲县一带。其应在商王畿西南部。
总之,周武王克商后把商王畿分给武庚,划分“殷”与“东”,前者包括“邶”、“鄘”,后者即“卫”,邶在商王畿以北的河南安阳殷墟,为霍叔所监; 卫在商王畿之东(今河南浚县、淇县),为管叔所监; 鄘大概在商王畿的西南部,为蔡叔所监。武庚虽然封有整个商王畿,但为了“守商祀”的需要,居在以北的殷墟,与霍叔驻守邶地的地望相合,所以《汉书·地理志》认为武庚是封在邶地。这种局面直到周成王平叛后才打破。
三、周成王平叛
周武王克商二年而亡,[86]周成王即位,周公辅政。《尚书大传》中说:“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87]这里的”摄政“,实际上是周公辅佐成王执政,[88]据西周铜器铭文,周公辅佐成王时期,一直用成王纪年,如扶风庄白村出土之墙盘(《集成》10175)与眉县杨家村新近出土之逨盘铭文,[89]确实未有将周公计入王系的; [90]2009年公布的西周早期铜器何簋中周公的纪年仍称“公”; [91]均可为证。因此这里的“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均就成王纪年而言。
《逸周书·作雒》:“(武王)成岁十二月崩镐,肂予岐周。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东徐奄及熊盈以略。周公、召公内弭父兄,外抚诸侯。九年夏六月,葬武王于毕。“周公被任命为辅政之臣而遭到了管叔等的猜忌,《尚书?金滕》:”武王既丧,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于国,曰:’公将不利于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无以告我先王。’“所说的管、蔡流言,目的就是为了发动叛乱。于是,三叔联合武庚以及商奄(在今山东曲阜东)等发动叛乱。
周成王二年,成王开始平叛。平叛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周成王二年的“克殷”,即镇压三监,平定“殷”、“东”为代表的商王畿,统帅为周成王。《尚书大传》:“二年克殷”,郑玄注:“诛管、蔡及禄父等也。“[92]《逸周书?作雒》:”二年,又作师旅,临卫政(征)殷,殷大震溃。降辟三叔,王子禄父北奔,管叔经而卒,乃囚蔡叔于郭凌。“”临卫政(征)殷“,”卫“即”东“为管叔所监,这说明卫已经攻下。“管叔盖逃入”殷“(即邶、鄘之地),故周军又据卫攻殷,结果王子禄父率领殷国的残余突围北奔,殷城于是崩溃而降,三叔就落入周军手里了。此次平叛的统帅是周成王,《系年》第三章:“成王屎伐商邑,杀彔子耿,飞廉东逃于商盖氏(即商奄——引者注)。“三监失败,武庚北奔,武庚亲信飞廉也东逃,平叛进入第二个阶段。
第二个阶段是成王三年的“践奄”,此次兵分两路:召公率军向北追击武庚; 成王与周公追击东逃飞廉。“践奄”者,主要是要平定商王畿以东地区。《逸周书·作雒》:“征熊盈族十有七国”。“盈”通“嬴”,[93]《系年》第三章曰“飞廉东逃于商盖氏。成王伐商盖,杀飞廉“,”商盖“即”商奄“,简文载秦人祖先飞廉逃入商奄,周公平叛后将一部分商奄之民西迁,而这些人正是秦人祖先,笔者认为《逸周书》所谓”征熊盈族十有七国“中即有秦人祖先飞廉族。又,《孟子?滕文公下》:“周公相武王诛纣,伐奄三年讨其君,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此处的”三年“,应指周成王三年。[94]此次平叛召公也参与了,故《史记·周本纪》曰:“召公为保,周公为师,东伐淮夷,残奄,迁其君薄姑。“召公乃追击北奔的武庚,周成王时期的大保簋(《集成》4140)曰:”王伐彔子,厥反,王降征命于大保,大保克敬,亡谴,王侃,大保锡休集土,用兹彝对命。“这里的彔子即清华简《系年》中的彔子耿,指武庚。[95]《系年》第三章:“飞廉东逃于商盖氏。成王伐商盖,杀飞廉。“”商盖“即”商奄“。此事发生于周成王三年,即《尚书大传》所谓的“三年践奄”。
成王平叛以后,开始建诸侯。《尚书大传》中说:“四年建侯卫”,意即成王四年普遍封诸侯之意。[96]而且据清华简《系年》可知,在普遍分封之前,周成王、周公“乃先建卫叔封于康丘”,这说明康叔的分封在此之前,那么究竟在何时?分封的地点——康丘——又在何处呢?下面,我们对这两个问题分别考述之。
四、康叔分封的时间与地点考
关于康叔的分封,传世文献所载语焉不详且多有歧义,而新出的《系年》正可补传世文献之不足。
《系年》第四章:“周成王、周公既迁殷民于洛邑,乃追念夏商之亡由,旁设出宗子,以作周厚屏; 乃先建卫叔封于康丘,以侯殷之余民。卫人自康丘迁于淇卫。“简文的”乃追念夏商之亡由,旁设出宗子,以作周厚屏“即《尚书大传》之”建侯卫“,开始普遍分封诸侯; 但在此之前,简文说“先建卫叔封于康丘”,可见康叔所封在大规模分封之前。而之所以要先封康叔,其目的是“以侯殷之余民”。之所以称“余民”,是因为“周成王、周公既迁殷民于洛邑”后所余之民。因此,康叔分封的时间在“周成王、周公既迁殷民于洛邑”之后。下面首先说“周成王、周公既迁殷民于洛邑”的时间。
(一)“周成王、周公既迁殷民于洛邑”的时间
《逸周书·作雒》载周成王“二年,又作师旅,临卫政(征)殷,殷大震溃。降辟三叔,王子禄父北奔,管叔经而卒,乃囚蔡叔于郭凌。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国,俘维九邑。俘殷献民,迁于九里。俾康叔宇于殷,俾中旄父宇于东。“这里征伐了”熊盈族十有七国“,为何所”俘“仅为”九邑“?孔晁注:“俘囚为奴十七国之九邑,罪重,故囚之。“[97]可见”九邑“之民是因为”罪重,故囚之“。那么,这“九邑”之民到底是哪些人?金兆梓推测说这些人正是当初附从武庚(原误为“康”——引者按)之乱,与周邦讨伐军作战的那些殷顽民、多士。[98]笔者以为这种推测是正确的。根据后文考证可知,这“九邑”之民先被迁到九里,后又迁至洛邑。
又,东汉贾逵《左传解诀》曰:“迁邶、庸之民于成周(即洛邑——引者按)”[99],《汉书·地理志》亦曰:“迁邶、庸之民于雒 ”邶(洛)邑“[100],《帝王世纪》:”(周公营成周,)居(邶)鄘之众“[101],据此可知这些所迁之殷顽民原本处于邶、鄘之地。那么所迁者为何仅为邶、鄘之民呢?上引《逸周书?作雒》:“二年,又作师旅,临卫政(征)殷,殷大震溃。降辟三叔,王子禄父北奔,管叔经而卒,乃囚蔡叔于郭凌。“上文已言卫即东为霍叔所辖,卫地之民应该早就降于周军,故周人能以卫作为根据地”征殷“,而”殷“正是邶、鄘之地。也就是说,二年“克殷”,主要是要征服邶、鄘之民,而且这些殷人也最顽固,所以“克殷”之后,周人就将邶、鄘之民俘获囚禁之,此即“俘殷献民”。[102]
这些所俘之“殷献民”,随后被“迁于九里”,孔晁注:“献民,士大夫也。九里,成周之地,近王化也。“[103]实际上,”殷献民“即殷遗民、殷顽民。[104]“九里”,清代学者于鬯考证是周之监狱,后来演变成为地名,[105]在今河南巩义南。[106]
那么,“俘殷献民,迁于九里”发生于何年?前文已述,“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国”是成王三年践奄事。但所俘者既然为武庚之民,而武庚在成王二年既已北奔,则“俘殷献民,迁于九里”可能发生于成王二年或三年。又,“俾康叔宇于殷,俾中旄父宇于东”发生在成王二年(详后文),因此这些殷民开始迁徙应在成王二年。可见,周成王二年克殷后,周成王把武庚所辖殷墟之民迁到九里囚禁之。
后不久,周人为了营建洛邑的需要,又将这些殷遗民从九里迁到洛邑。[107]据《尚书·多方》载,成王三年五月这些殷遗民已经到了洛邑附近。《尚书·多方》:“惟五月丁亥,王来自奄,至于宗周。周公曰:’王若曰:猷告尔四国多方惟尔殷侯尹民,我惟大降尔命……’“”王曰:’嗚呼!猷告尔有方多士,暨殷多士:今尔奔走臣我监五祀,…… 克阅于乃邑谋介尔,乃自时洛邑,尚永力畋尔田。’“这里的”监五祀“是周武王二年加成王三年,亦即第五年为成王三年。“王来自奄”,说明是践奄之后。“克阅于乃邑谋介尔,乃自时洛邑,尚永力畋尔田”,意思是只要能相安于你们的居邑,当设法相助你们,你们在洛邑这地方住下来,长期用力于田亩。可见,周成王三年五月丁亥,殷人已经到了洛邑附近。据此,成王三年已经利用殷遗民建设成周了。
周成王五年,成周建成,[108]《尚书序?多士》:“成周既成,迁殷顽民。周公以王命诬,作《多士》“[109]这些顽民、遗民多数即为在邶、鄘之地附于武庚参加叛乱之兵士,故常称呼为”多士“。成周的修建,主要是为了让殷遗民居住,《尚书序》的含义是“成周城建好后,让殷遗民由城外迁入成周”。
这里有必要说明“成周”与“洛邑”的关系。根据最近的考古发现来看,西周时期周公所营建的“洛邑”、“成周”、“新邑”名相异而实同,地点在今河南洛阳的瀍河两岸。[110]前文已述,这些迁至洛邑的殷遗民,主要是邶地(今安阳殷墟)与商王畿西南部的鄘地之民,这部分人于成王二年从邶(殷墟)、鄘迁至九里进行囚禁。后又因营建成周的需要,三年已经到了洛邑,开始营建成周。成王五年,这些殷遗民迁到成周城内。也就是说,笔者认为这些迁到洛邑的一部分殷民正是武庚所封殷墟之民。考古发现证实了这种说法。
考古发现证明,周公所营建的成周或洛邑在今河南洛阳东部瀍河两岸。具体位置在今史家沟以东、焦枝铁路以西、北窑村以南、洛阳老城南关以北的瀍河两岸,东西约3公里、南北约2公里。[111]在洛阳老城北北窑村西瀍河两岸集中分布着周人墓葬。在瀍河以东,集中分布着殷遗民墓。大概有一百多座。[112]其中1952年考古工作者在瀍河以东下瑶村西区发掘12座殷人墓的第159号墓,为长方形竖穴墓,墓底中部是长方形椁室,正中有腰坑,椁室四边有夯土二层台,这种作法与安阳殷墟附近的殷代小墓作法完全相同; 而且,墓葬中出土的铜铲(65号),形制与安阳大司空村第3号殷墓出土的铜铲完全相同。考古学家推断可能是殷遗民的墓葬。[113]另外在洛阳老城北瀍河的西岸西周王室铸铜作坊遗址发现了近百座殷遗民墓。[114]在西周贵族墓南面,洛阳瀍河西岸二级台地上,发现了一处面积10万平方米以上的铸铜作坊遗址,其中第一期遗址属于西周早期(约相当于西周初至成王、康王时期)。[115]从发掘的结果看,该遗址所反映的铸铜技术与殷墟苗圃北地铸铜遗址所反映的技术一脉相承,因此学者认为,该铸铜遗址作坊可能是周初殷墟迁入洛阳的,当年作坊内的生产者应是安阳迁入洛阳的“殷人”。[116]笔者认为,这些殷人很可能是武庚所辖殷墟之地的殷遗民,因此所迁殷遗民除了“多士”外,还有一些手工业者。
综上可见,周成王二年克殷后,开始将殷遗民大量地从殷都迁往九里(今河南巩义),到成王三年五月,这些殷遗民已经到了洛邑。周成王五年,“新邑”建成以后,殷遗民再从洛邑城外迁入城中,此即《尚书序》所谓的“成周既成,迁殷顽民”。简文说“周成王、周公既迁殷民于洛邑”实际上是指成王二年至三年将殷民从邶、鄘之地迁到九里再到洛邑附近之事。
(二)从“乃先建卫叔封于康丘”看康叔的分封时代与地点
关于康叔分封,主要有以下记载,为便于说明,我们按照文献的时代顺序列举如下,并作以考证。
(1)沬司徒疑簋:“王来伐商邑,诞令康侯啚(鄙)于卫,沬司徒疑眔啚(鄙),作厥考尊彝。。“(《集成》4059,西周成王)
铭文的“王”指周成王,“王来伐商邑”,对应于《系年》第三章的“成王屎伐商邑”,是指周成王二年平叛三监之乱。“鄙于卫”,唐兰说:“鄙,边境。《左传》昭公十六年:’公子皆鄙’,注:’边邑也。’“[117]李学勤说:”铭中的’啚’读为’鄙’,应该解释为划定国土的边境地区。王在征伐商邑,平定叛乱之后,分封康侯,确定其边鄙自然是必要的步骤。“[118]按,”鄙“一方面有划定边境之义; 另一方面也有“边邑”之义,如《左传》僖公三十年郑大夫烛之武对秦伯说“越国以鄙远”,杜预注:“设得郑以为秦边邑”,[119]可证。铭文说“令康侯鄙于卫”,说明未封在卫。据(2)《逸周书?作雒》“俾康叔宇于殷,俾中旄父宇于东”,“宇”是权力所及的疆域; [120]与“鄙”义同。据此,康叔虽封在“殷”,但“东”也是康叔所辖之边邑,只是让其子中旄父管理,此即“令康侯鄙于卫”。
(2)《逸周书?作雒》:“二年,又作师旅,临卫政(征)殷,殷大震溃。降辟三叔,王子禄父北奔,管叔经而卒,乃囚蔡叔于郭凌。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国,俘维九邑。俘殷献民,迁于九里。俾康叔宇于殷,俾中旄父宇于东。”
“俾康叔宇于殷,俾中旄父宇于东”即(1)中“令康侯啚(鄙)于卫”,在周成王二年克殷之后。“中旄父”即康叔子康伯,[121]“东”即“卫”。如此可见,周成王是让康叔父子来管理殷(包括邶、邪)与东(即卫),实际上东地也尽封给了康叔,因为父子一体,受命不封子,《白虎通·封公侯》说:“受命不封子者,父子手足无分离异财之义”,可证。据此,武庚与三监平定后,周成王将“殷”(邶、鄘)与“东”(卫)都封给了康叔,只是由于地域辽阔,成王又让康叔之子中旄父去管理。
(3)《左传》定公四年:“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选建明德,以蕃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于周为睦。…… 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绵茷、旃旌、大吕,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锜氏、樊氏、饥氏、终葵氏; 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取于有阎之土以共王职; 取于相土之东都以会王之东搜集。聃季授土,陶叔授民,命以《康诰》而封于殷虚。皆启以商政,疆以周索。“杜预注:”殷虚,朝歌也。”[122]
康叔分封在周成王时期,且此时周公相王室; 与(4)《系年》简文对照,二者相合。又,《左传》说康叔被封的地点是“殷虚”,杜预说“殷虚”指朝歌。实际上根据(4)《系年》可知,“殷虚”实指安阳洹水两岸之殷墟(详后)。
另外,分康叔之民是“殷民七族”,郭宝钧认为,陶氏即陶工,施氏即旌旗之工,繁氏即马纓之工,锜氏即锉刀工或釜工,樊氏篱笆工,终葵氏是锥工。[123]实际上,在殷墟范围内发现了多处手工业作坊,包括苗圃北地、孝民屯西、薛家庄和小屯东北地、大司空村发现铸铜作坊5处,大司空村、北辛庄制骨作坊2处,另外还发现了一些制作玉器、骨器、陶器等作坊的线索,从作坊的分布分析,可能属于居住在殷墟的各个族邑。[124]笔者认为,分给康叔的这些人正是殷墟之手工业者。
(4)《系年》第四章:“周成王、周公既迁殷民于洛邑,乃追念夏商之亡由,旁设出宗子,以作周厚屏; 乃先建卫叔封于康丘,以侯殷之余民。卫人自康丘迁于淇卫。”
关于康叔被封的时间,核诸文献应该在周成王二年克殷之后,理由有如下两点:
第一、根据(1)沬司徒疑簋“诞令康侯啚(鄙)于卫”在成王二年克殷之后,而“诞令康侯啚(鄙)于卫”对应于(2)《逸周书?作雒》:“俾中旄父宇于东”,故“俾康叔宇于殷”也在成王二年。“俾康叔宇于殷”正是简文的“先建卫叔封于康丘”,说明后者也是成王二年。
第二、简文“周成王、周公既迁殷民于洛邑”指周成王二年开始将邶、鄘之民迁往九里,不久迁往洛邑之事。何谓“先建”?“建”,当读为《左传》隐公八年:“天子建德”之“建”,杜注:“立有德以为诸侯”[125],即“建”乃立诸侯之义。“先建”康叔于“康丘”者,当为先立康叔于康丘为诸侯之义。这里的“先”,相对于简文前“乃追念夏商之亡由,旁设出宗子,以作周厚屏”所言的普遍分封诸侯之事,“先建”说明康叔的始封在此之前。[126]据(1)、(2)可知是成王二年“克殷”后事。
综上可见,周成王二年克殷之后,将邶、鄘之民外迁,随后就封康叔于康丘。因此,康叔的分封在周成王二年。[127]
以下再讨论康叔被封的地点——康丘。对其地望,李学勤“推想当在邶、鄘、卫三地中的卫地境内,……’卫’是大名,’康丘’是其中作为都邑的地点”。[128]朱凤瀚不同意康丘属于卫说,他说:“简文下继言’卫人自康丘迁于淇卫’,则是言康侯受命将其族属、部众由康丘迁入卫地之内,即进入原商王畿区域。可见康丘不会在卫地范围内,而是在卫地之外,但既要监督殷余民必亦不会距卫地太远,应在卫之临近地“[129]。笔者认为朱先生的反驳是正确的。路懿菡说:“卫祝陀所说的’殷虚’指的应是安阳殷都故地。《系年》简文所载的’康丘’之地很可能即位于此区域内。”[130]
康丘在殷墟是正确的,但正如前文所言,邶亦在殷墟; 故邶应是大名,而康丘则是其中作为都邑的地点。下面我们对此说进行论证。
首先,将《系年》与(3)、(5)相对照,不难发现“康丘”即指“殷虚”和“商墟”,二者所指为同一地。关于“殷虚”,上引(3)杜预注认为殷虚指朝歌,这一说法长期以来占有统治地位,鲜有异议。[131]值得注意的是,“殷虚”也指安阳洹水之殷墟。《史记·项羽本纪》:“项羽乃与期洹水南殷虚上。“裴骄《集解》:
应劭曰“洹水在汤阴界。殷墟,故殷都也“。瓚曰“洹水在今安阳县北,去朝歌殷都一百五十里。然则此殷虚非朝歌也。《汲冢古文》曰’盘庚迁于此’。《汲冢》曰:’殷虚南去邺三十里’,是旧殷虚,然则朝歌非盘庚所迁者。”
唐司马贞《索隐》引《竹书纪年》曰:“盘庚自奄迁于北蒙,曰殷虚。南去邺州三十里。“[132]据此可见,今河南安阳洹水两岸也有”殷虚“。裴骄《集解》引瓚说“此殷虚非朝歌也”,如此则说明“殷虚”在朝歌与安阳均有。又,简文说“卫人自康丘迁于淇卫”,说明“康丘”不在“淇卫”; 李学勤认为是“滨于淇水的朝歌”; [133]如此则“康丘”所在之“殷虚”必是位于安阳洹水两岸之殷墟。
其次,(5)《史记·卫世家》说“以武庚殷余民封康叔为卫君,居河、淇间故商墟”,可见康叔所封之“殷余民”原本为武庚所辖; 而据前文所述,武庚所辖之殷余民就在安阳之殷墟; 如此说明康丘就在武庚故地,亦即安阳之殷墟。
再次,顾颉刚说:“古者建都必择丘陵,故齐为营丘、鲁为曲阜、燕为蓟丘、蔡有蔡冈、成周有郏邫。“[134]康丘与此类似,正是康叔在邶地建立都邑之地点,且此处地势应该较高。
总之,康丘在安阳之殷墟,这是可以确定的。
所谓“侯殷之余民”者,这里的“侯”通“候”,就是负责监视、监管之义。[135]所谓“余民”对应于(6)《尚书序》:“以殷余民封康叔”之“余民”,指周成王二年将殷民开始迁走后所余之民。《史记·管蔡世家》载平定武庚及三监叛乱后,“而分殷余民为二:其一封微子启于宋,以续殷祀; 其一封康叔为卫君,是为卫康叔“。据此,则周成王将所余之殷民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封给微子,另一部分封给康叔。分给康叔的殷余民,《史记·卫世家》说“以武庚殷余民封康叔”,正是邶地之民,亦即上引(3)《左传》所谓“殷民七族”。这些殷余民主要是武庚所在“邶”地(殷墟)的手工业者,那么分给微子启的很可能就是鄘地之余民。《史记·宋世家》:“周公既承成王命诛武庚,杀管叔,放蔡叔,乃命微子开(启)代殷后,奉其先祀,作《微子之命》以申之,国于宋。微子故能仁贤,乃代武庚,故殷之余民甚戴爱之。“这个”宋“即在今河南商丘,也就是说成王二年克殷后,封微子,然后把鄘地之殷余民分给宋,所以这些人也迁到了宋国。
《史记·三王世家》说:“康叔后扞禄父之难。“《后汉书·苏竟传》载苏竟《与刘龚书》说:”周公之善康叔,以不从管、蔡之乱也。“清代学者皮锡瑞说:”管、蔡流言作乱之时,京师亦必有从乱者,惟康叔不从乱; 周公东征禄父,康叔当有协赞之功,故公深知其能,使监殷民于卫。“[136]皮氏所说基本正确,惟”使监殷民于卫“当作”监民于康“。
简文说“卫人自康丘迁于淇卫”,这应该在康叔为司寇之后。周成王三年践奄之后,就把康叔调到周王朝担任司寇,此即《史记·卫世家》所谓“成王长,用事,举康叔为周司寇”,《管蔡世家》所谓“康叔…… 有驯行,于是周公举康叔为周司寇,…… 以佐成王治“。于是,卫人为了集中管理殷遗民的需要,出现了《系年》所谓的“卫人自康丘迁于淇卫”。
(5)《史记?卫世家》:“周公旦以成王命兴师伐殷,杀武庚禄父、管叔,放蔡叔,以武庚殷余民封康叔为卫君,居河、淇间故商墟。周公旦惧康叔齿少,乃申告康叔曰:“必求殷之贤人君子长者,问其先殷所以兴,所以亡,而务爱民。“告以纣所以亡者以淫于酒,酒之失,妇人是用,故纣之乱自此始。为梓材,〔一〕示君子可法则。故谓之康诰、酒诰、梓材以命之。”
司马迁说封康叔之封在「杀武庚禄父、管叔,放蔡叔」之后,后者即二年克殷。实际上武庚未被杀死而是北奔。武庚向北逃跑后,成王二年后周人将大部分殷民迁走,所余之殷民封给康叔,司马迁说「封康叔为卫君」,「居河、淇间故商墟」。“前文已述,”河、淇间“即《系年》所谓的”淇卫“——此处既谓”河、淇间故商墟“,则与(2)中所谓安阳之殷墟不同——在今河南淇县,时属邶、鄘、卫之卫,而此事在成王三年后。那么具体在何年呢?司马迁又曰将康叔封为“卫君”时,且周公申告康叔以《康诰》、《酒诰》、《梓材》。我们知道在周初金文中称叔封就是康侯,如康侯方鼎(《集成》2153)铭云:「康侯丰作宝尊」等。其子称「康伯」,见于康伯簋盖(《集成》3721)、康伯簋(《集成》3720)等。至于称「卫君」于何时?确定的时间点应是周公申告康叔以《康诰》、《酒诰》、《梓材》之际,而据笔者研究,此三篇制作于成王四年[137],故笔者认为称「卫君」在成王四年。[138]
(6)《尚书序》:“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余民封康叔,作《康诰》、《酒诰》、《梓材》。”
《书序》也说成王封康叔在“伐管叔、蔡叔”,即成王二年克殷之后。“余民”者,清代学者陈启源说:“成王既黜殷,迁顽民于洛邑,迁之未尽者则以授康叔,使为之君而教之。《书序》谓’以殷余民封康叔’者,此实録也“[139]。所言甚是。
(7)班固《汉书·地理志》:“《书序》曰’武王崩,三监畔’,周公诛之,尽以其地封弟康叔,号曰孟侯,以夹辅周室;迁邶、庸之民于雒邑,故邶、庸、卫三国之诗相与同风。”
班固说康叔的分封也是在成王二年克殷之后,然后把整个邶、鄘、卫之地全都分给康叔,亦即(2)所谓的“俾康叔宇于殷,俾中旄父宇于东”。班固又说说“迁邶、庸之民于雒邑”,据此可知卫地之民则未迁。因此,所谓的未迁走所余之殷民只能是邶、鄘之民,据(4)可知,邶地之余民分给康叔,鄘地之余民分给了微子。周成王四年康叔为司寇后,封给康叔的邶地之民也迁到卫国,所以“邶、庸、卫三国之诗相与同风”。对此,孙诒让说:“盖周公以武庚故地封康叔,实尽得三卫全境,以其地闳广难治,故依其旧壤,仍区殷、东为二,以其子弟别治之。…… 是中旄宇东,虽专治其邑,而仍属于其父,则与三监分属微异。逮康叔卒,康伯嗣立,而东遂不复置君,故采《诗》者,于三卫不复析别。是三卫始则三监鼎峙; 中则殷、东虽分二宇,而实统于一属; 终乃夷东为邑,而与殷并合为一; 其事可推迹而得也“[140]。孙氏谓康叔时已占有殷(邶、鄘)、东(卫)全境,这是正确的; 但谓康叔死后,康伯时殷、东合而为一,“东遂不复置君”,由(4)、(5)、(6)、(7)可知并不准确。准确地讲,成王四年卫人由康丘迁到卫,殷(邶、鄘)遂不复置君。
综上可见,周成王二年平定武庚与三监叛乱后,武庚北奔,周成王将殷遗民从殷墟迁到九里囚禁,然后将所余之民——包括《左传》中的“殷民七族”——分给康叔,让其监管。康叔分封的地点——康丘——就在殷墟。由于商王畿地域辽阔,成王又命康叔管理“殷”,让其子中旄父管理“东”。成王三年践奄以后,四年康叔到周王朝任司寇,康叔所辖之民也就迁到卫,康叔得称「卫君」,此后康伯及其后代亦可称「卫君」了。
五、邶、康丘、汤丘与殷墟的关系
上文考证邶、康丘都在安阳之殷墟,那么这三者的关系如何呢?殷墟又是如何形成的呢?这实际上牵涉到周初的历史,下面对此进行说明。
首先说邶、康丘与殷墟的关系。前文已述,殷墟在商王畿之北,武庚居于此以祭祀商先王。而霍叔也在此驻军,所以《汉书·地理志》认为武庚是封在邶地。
周成王克殷之后,将此地封康叔,康叔分封的具体地点在康丘。康丘是其中作为都邑的地点。邶是殷墟的一个邑,地域应该较大; 康丘与殷墟的关系是小地名与大地名的关系。那么,康丘因何得名呢?笔者认为应跟“汤丘”有关,有学者认为“汤丘”即“康丘”,[141]这是可能的。
清华伍《汤处于汤丘》曰“汤处于汤丘”。[142]“汤”与“康”古音很近,楚文字中也有很多通假的例子。[143]“丘”者,《说文·丘部》:“丘,土之高也。“本指土高之名,只有小地名用”丘“。“丘”也指墟,《楚辞·哀郢》:“曾不知夏之为丘兮。“注:”丘,墟也。“[144]汤丘者,是因为此地是商王汤旧居之地。
《史记·殷本纪》载:“汤始居亳”,“帝盘庚之时,殷已都河北,盘庚渡河南,复居成汤之故居,迺五迁,无定处。殷民咨胥皆怨,不欲徙。盘庚乃告谕诸侯大臣曰:’昔高后成汤与尔之先祖俱定天下,法则可修。舍而弗勉,何以成德!’乃遂涉河南,治亳,行汤之政,然后百姓由宁,殷道复兴“,周武王克商后”封纣子武庚禄父,以续殷祀,令修行盘庚之政“。司马迁此处根据的是《吕氏春秋·慎大》。[145]据《史记》,盘庚居成汤之地是“行成汤之政”,纣子武庚禄父“修行盘庚之政”很可能就是复居成汤之故居。正如清代学者姚鼐说:“殷贤君多矣!独行盘庚之政者,正以其始迁居殷故也。《正义》引《竹书纪年》’自盘庚徙殷至纣之灭…… 更不徙都,纣时稍大其邑。’按,《竹书》…… 更不徙都之说不谬。“[146]这表明从战国以至秦汉都流传着武庚所居之地是商汤、盘庚旧居之说法。前文已述,康叔所封之地“康丘”就是武庚旧地,这说明“康丘”的得名很可能源于“汤丘”。
根据考古发现,商早期的都城主要有两座,一是位于河南郑州市区的郑州商城,二是位于河南偃师市西南的偃师商城。有学者指出郑州商城是商前期的主都,而偃师商城则是陪都。[147]笔者认为,跟“汤丘”有关的考古学文化,目前主要有下七垣文化漳河型的安阳孝民屯遗址、[148]梅园庄一期[149]和小屯西地遗址。[150]刘一曼认为,属于殷墟“梅园庄一期”文化遗存的安阳孝民屯遗址、梅园庄1期,较殷墟一期早,时间跨度较大、持续时间较长,早段是先商晚期,晚段进入了商代早期; 小屯西地遗址大体上属于先商时期。[151]1997—1998年考古学家通过对洹河流域的调查,发现下七垣文化阶段及早商阶段,洹河流域的居民点分布尚未出现规模显赫的邑聚,可能先商时期商人的政治中心不在安阳地区。[152]这些文化有可能就是商汤暂时居于“汤丘”的文化遗存。无论如何,汤丘在殷墟也是有考古学证据的。[153]
汤丘既然是商汤之旧居,所以周成王把康叔封在此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他继承殷王商汤之政,来统治殷余民。《左传》定公四年载康叔分封时,“命以《康诰》而封于殷虚。皆启以商政,疆以周索“,由《系年》可知,此”殷虚“就是康丘,也是成汤之旧处地——汤丘。这里的“启以商政”,如果联系到盘庚“行成汤之政”,纣子武庚“修行盘庚之政”,不难看出康叔所“启”之“商政”正是“成汤之政”。《尚书·康诰》:“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丕远,惟商耇成人,宅心知训。“清代学者朱骏声曰:”殷先哲王,汤、太甲、太戊、祖乙、盘庚、小乙、武丁也。“[154]也是讲以成汤为代表的殷先王。如此看来,成王封康叔于“汤丘”,实际上就是为了让他继承以商汤为代表的商先王政策,这就是《左传》所谓的“启以商政”。
由上述分析可见,康叔被封之前,此地即名“汤丘”。但是,叔封之称“康叔”,分封时的命辞也称为“康诰”,说明叔封封此地时已经称“康丘”。那么,到底从什么时候由“汤丘”变成“康丘”的呢?
笔者认为“汤丘”改成“康丘”时间就在康叔被封时。之所以如此改,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康叔被封在此,又不能称“汤叔”——因汤是商先王名号,所以将此地命名为与之同音的“康”,称为“康丘”,叔封也才被称为“康叔”。又,“汤”与“康”可互作,如上博简《曹沫之阵》简65“亦唯闻夫禹、康(汤)、桀、纣”,就直接把“康”作“汤”了。另一方面,“康”也是一种美称,这种改动实际上也代表成王对叔封的期望与冀预。成王四年对康叔的诰辞《尚书·康诰》中,有很多“康”字,如“用康保民”、“用康乂民”、“迪吉康”、“康乃心”,代表成王对康叔的一种期许,诚如清代学者皮锡瑞说:《康诰》之所以以“康”字“名篇者,疑康叔生即以康为号,…… 史公分别《康诰》、《酒诰》、《梓材》之义,以务爱民属之《康诰》,则’康’当取爱民为义。《康诰》一篇,云……’康’字甚多,疑康叔之康,即以此为号“[155]。
《史记·卫康叔世家》:“卫康叔名封,周武王同母少弟也。“据此可知,”卫康叔“是周武王的同母幼弟,名为”封“,”叔“其字[156]。关于叔封何以称“康”,古有两说:一认为是国名。东汉古文家马融曰:“康,圻内国名。“(《尚书注》)[157]”圻内“即”畿内“。三国时期的王肃《康诰注》云:“康,国名,在千里之畿内。既灭管、蔡,更封为卫侯“[158]。伪《孔传》:“康,圻内国名。“[159]二认为是谥号。郑玄认为“康”是谥号。[160]两种说法,从汉代以来争论不休。从《系年》来看,叔封之所以称“康”就是因为“康丘”而来,因此“康”是国名说显然是正确的。
总之,邶是霍叔的驻军点,“汤丘”就在河南安阳之殷墟,汤曾经居处于此,故名。周成王二年康叔封于此,将其改称“康丘”。“康丘”就是“汤丘”,与战国至秦汉流传的武庚所居之地是商汤、盘庚旧居这种说法相符。
六、殷墟的形成与周初的历史变迁
上文已述,邶、康丘就在安阳之殷墟,那么殷墟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殷墟古作”殷虚“,最早见于《左传》定公四年,曰:”分康叔…… 殷民七族…… 命以《康诰》而封于殷虚。“从文献上看,殷墟作为王都是从盘庚开始的,《尚书·盘庚》:”盘庚迁于殷。“《史记·殷本纪》正义引《古本竹书纪年》:”自盘庚徙殷至纣之灭…… 更不徙都,纣时稍大其邑,南距朝歌,北据邯郸及沙丘,皆为离宫别馆。“但根据考古发现,殷墟的主体遗址是从武丁开始的。1999年发现的洹北商城,与小屯晚商宗庙宫殿区相距仅1公里多。学者多认为盘庚所迁之“殷”在洹北商城,在经历盘庚、小辛、小乙后,武丁将宫殿区由洹北商城移到洹河南岸的现今小屯一带。[161]
关于殷墟作为都城的下限,上引《古本竹书纪年》说是一直持续到商纣帝辛时期,这是一说。另一说是帝乙时期迁都到朝歌,一直到纣王帝辛,如《史记·周本纪》正义引《帝王世纪》:“帝乙复济河北,徙朝歌,其子纣仍都焉”,又引《括地志》曰:“纣都朝歌在卫州东北七十三里朝歌故城是也。本妹邑,殷王武丁始都之“。王国维以殷墟卜辞所祭祀商王一直到康祖丁(康丁)、武祖乙(武乙)、文祖丁(文丁),说明“帝乙之世尚宅殷虚,《史记正义》引《竹书(纪年)》独得其实”。[162]所以学者多认同《古本竹书纪年》的说法。在考古上,唐际根认为,殷墟一期早段文化面貌过于个性化,而一期晚段则表现出与殷墟二、三、四期之间强烈的共性与自然连续性。[163]殷墟第四期(帝乙、帝辛)时期文化并未衰落。[164]正如前文所提到的,殷墟文化第四期最末阶段(IV5)的遗存文化属性可归于商文化,但其年代已进入西周初年,说明殷墟文化一直持续到西周初年。那么,殷墟文化废止于何时呢?从文献角度来说,就是殷何时成为“墟”。
《史记·宋世家》曰:
于是武王乃封箕子于朝鲜而不臣也。
其后箕子朝周,过故殷虚,感宫室毁坏,生禾黍,箕子伤之,欲哭则不可,欲泣为其近妇人,乃作《麦秀之诗》以歌咏之。其诗曰:“麦秀渐渐兮,禾黍油油。彼狡僮兮,不与我好兮!“所谓狡童者,纣也。殷民闻之,皆为流涕。
《宋世家》说武王时期箕子朝周经过“殷虚”,当时已经“宫室毁坏”。这是否意味着武王时期殷已经成为“墟”了?实际上,《宋世家》的上述记载是有问题的。清代学者简朝亮早就注意到这个问题,他说:
史迁…… 言箕子朝周者,非也。《大传》固以其诗为微子将往朝周而作矣。夫微子以客而朝周,可也; 箕子以臣而朝周,不可也。《史记》云“所谓狡童者,纣也”,亦非也,…… 此盖谓纣子武庚也。殷所以为虚,武庚之叛也。[165]
据简氏所言,《宋世家》里的“箕子”当作“微子”,而“狡童”实际上指的是纣子武庚,殷成为墟,“宫室毁坏,生禾黍”,实际上是武庚叛乱之后事。
又,《宋世家》这段话也见于《尚书大传》,只是把“箕子”改作“微子”。《尚书大传·微子之命》:
微子将往朝周,过殷之故墟。见麦秀之蔪蔪。曰:“此父母之国,宗庙社稷之所立也。“志动心悲,欲哭、则为朝周,俯泣、则近妇人,推而广之,作《雅声》。歌曰:“麦秀蔪蔪兮,禾黍,彼狡童兮,不在好兮。”[166]
清代学者王闿运《补注》说:“《序》云:’克殷杀武庚。’殷,谓禄父也,禄父武庚盖于战死,故改制收殷故地,别封微子为上公“,”壮佼而如童子,谓禄父武庚“。[167]王氏认为微子朝周过殷墟也在克殷杀武庚之后。
笔者认为,简朝亮、王闿运之言是正确的。正如前文所论,牧野之战商人倒戈,所以未对宫室造成毁坏。武王克商后,又将整个商王畿分给武庚,商人自然也不会自毁宫室,因此,殷成为墟只能是武庚叛乱之后事。
周成王二年克殷,武庚北奔,亲信飞廉也东逃,武庚所盘踞之殷地也落入周人之手。而殷之所以成为“墟”,有两个原因:
第一、周人的大规模破坏。《吕氏春秋·古乐》:“成王立,殷民反,王命周公践伐之。“《淮南子·齐俗》:”武王既没,殷民叛之,周公…… 克殷残商。“”残“、”践“音近可通,即古书常见的”翦“,甲骨金文形作”“,后来演变为形声字”戬“,为诛灭之义,「残」、「践」均为借字。[168]所谓“践”,《尚书大传》说:“遂践奄。践之云者,谓杀其身,执其家,潴其宫。“[169]《说文·水部》:”潴,水所亭也。“”“潴其宫”是说不仅把宫室毁了,而且在原地基上挖掘出一个池塘,这是最严重的惩罚。《尚书大传》所说虽然针对奄国,笔者怀疑实际上周人对武庚所盘踞之殷墟也进行过大规模的毁坏行为。事实上古人对于反叛之国的惩治是非常严厉的,《汉书·王莽传》载“竦因为嘉作奏曰”:“臣闻古者畔逆之国,既以诛讨,(而)〔则〕猪其宫室以为污池,纳垢浊焉,名曰’凶虚’,虽生菜茹,而人不食。四墙其社,覆上栈下,示不得通。“周初青铜器何簋载”隹八月公夷殷年, 公赐何贝十朋, 乃令何司三族, 为何室“[170]。李学勤认为,“夷”有夷灭的意思,“夷殷”即“墟殷国”,《古本竹书纪年》称盘庚迁殷以至于纣,朝歌为纣所居处的“离宫别馆”,这样看来被夷灭的殷主要是指今安阳洹上的殷墟。[171]今按,夷确有破坏、夷平之义,《国语·周语》:“是以人夷其宗庙,而火焚其彝器。“《史记·项羽本纪》载项羽”遂北烧夷齐城郭室屋“。据何簋,周人在平定武庚叛乱后,夷平了武庚所居的宫殿,这件事影响很大,所以周人以此纪年。
实际上,周人破坏殷墟在考古上也有证据。位于安阳西北郊武官村和侯家庄北的西北岗是殷代王陵区,王陵区的14座大墓均遭到多次盗墓,其中以早期盗掘坑最为严重,墓室内的随葬品几乎被洗劫一空,所剩物极少。考古学家考察这些盗墓行为具有明显的共时性特征,而且是由一定规模的人有组织、有预谋地在光天化日下明目张胆进行的; 这些盗掘行为发生在西周早期。据这些特征,学者推断实施这些盗掘行为的正是周人的政府,时间就在平定武庚叛乱之后。[172]另外,1933年10月—12月对殷墟小屯村北的发掘中,考古学家石璋如发现了竖房屋柱的铜础,有的铜础周围有许多如豌豆大小的铜珠,他推断这是铜础被火焚镕后入土凝结而成; 而且在垫铜础的石卵上还有层红烧土,掺杂着木炭等。根据这些现象,石先生推断殷墟宫殿的摧毁和都城的废弃,其中当含有火烧的成分。[173]笔者以为这些都是周人平定武庚叛乱后毁坏殷墟宫殿的证据。
第二、周人将殷墟的殷遗民迁徙所致。《荀子·儒效》:“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属天下,恶天下之倍周也。…… 杀管叔,虚殷国。“杨倞注:”虚,读为墟。…… 墟殷国,谓杀武庚,迁殷顽民于洛邑,朝歌为墟也。“[174]实际上,”虚殷国“指的是安阳之殷墟,但杨氏认为迁殷民导致安阳殷都成为墟是对的。
周成王二年,周人将邶、鄘之民迁于九里进行囚禁,把未迁所余之殷民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邶地之民分给康叔,另一部分鄘地之民则分给微子。成王四年将康叔之民又迁到“淇卫”,如此则邶、鄘之地就没有殷民了,正如清代学者陈启源所说:“成王作洛之后,殷顽民尽徒下都(指洛邑——引者按)。封伯禽又以殷民六族,赐之留处故土者殆无几。…… 封康叔时,民得留者多在卫,其邶鄘两国已成旷土“[175]。
由上可见,殷之成为墟发生在周成王二年克殷之后。笔者认为殷墟文化的结束应在此时。这种看法与考古发现是吻合的。
七、结论
本文所论涉及与今日史家多有异议之周初重要史事及历史地理,现将主要观点归纳如下:
(一)“三监”的性质。周武王克殷之后,周人实力还不足以实现对商王畿完全统治,因此所设之“三监”(即管叔、蔡叔、霍叔)主要是军事性质的,三监所驻守的邶、鄘、卫不是“三监”之封国,而是军事据点。
(二)“殷”、“东”与邶、鄘、卫的关系及其地望。周武王克商后把商王畿分给武庚,划分为“殷”与“东”,前者包括邶、鄘,后者即卫。邶位于商王畿以北,今河南安阳殷墟,为霍叔所监; 卫在商王畿之东(今河南浚县、淇县),为管叔所监; 鄘大概在商王畿的西南部,为蔡叔所监。武庚虽然封有整个商王畿,但为了“守商祀”的需要,居于王畿北部的殷墟,与霍叔驻守邶地地望相合,所以《汉书·地理志》认为武庚封在邶地。这种局面直到周成王平叛后才被打破。
(三)周成王平叛的过程及其年代。周成王平叛总体上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成王二年克殷,第二阶段是成王三年践奄。二年“克殷”后,成王将邶、鄘之民中的大部分迁到九里囚禁之,后又因营建成周的需要从九里迁到洛邑。未迁走所余之殷民分为两部分:邶地之民分给康叔; 鄘地之民分给微子启,不久被迁到宋国。
(四)卫分封的年代与地点。康叔的分封并非以往学者所谓的武王时期或者成王四年等,而在周成王二年。邶、鄘之民被迁后,成王将整个商王畿分给康叔管辖,具体分封的地点是康丘(即在邶地),所封民即殷墟之民。由于地域辽阔,康叔与其子中旄父分而治之,前者管理的地方是“殷”,后者是“东”。成王三年践奄之后,四年康叔到周王朝任司寇,其所辖之民又从康丘迁到卫。
(四)殷墟形成的时间与原因。邶、康丘就在今河南安阳之殷墟。殷墟之所以形成,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克殷之后周人为了报复,对殷实行了大规模的破坏行动。二是殷墟之民绝大部分迁到了洛邑,所余部分开始分给康叔,不久由于殷之破坏、康叔到周王朝担任司寇,所余之殷遗民也迁到卫,导致殷地逐渐荒芜,成为“墟”。殷之成为墟发生在周成王二年克殷之后。
附记:本文原刊于(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91本第4分(2020年12月),第579—631页。
参考文献
[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周金文集成》(简称 《集成》),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
[2] 这方面学者的成果颇丰,现当代比较重要的如顾颉刚《周公东征史事考证》之《甲 三监人物及其疆地》、《丙 三监及东方诸国的反周军事行动和周公的对策》、《丁 周公东征的胜利和东方各族大迁徙》、《东土的新封国》,氏著:《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十(下),北京:中华书局,2011,第607—637,687—704,704—1031,1031— 1070页; 刘起钒《周初的“三监”与邶、鄘、卫三国及卫康叔封地问题》,氏著,《古史续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514—543页; 王玉哲《周初的三监及其地望问题》,《古史集林》,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245—255页; 陈恩林《鲁、齐、燕的始封及燕与邶的关系》,《历史研究》1996年第4期等等。
[3] 对此问题可参:蒋善国《尚书综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237—240页。
[4] 李学勤:《清华简〈系年〉解答封卫疑谜》,《文史知识》2012年第2期,第15页。
[5] 这方面的代表性成果如李学勤《清华简〈系年〉及有关古史问题》,《文物》2011年第3期; 《清华简〈系年〉解答封卫疑谜》,《文史知识》2012年第3期; 《由清华简〈系年〉重释沬司徒疑簋》《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3年第3期。董珊《清华简〈系年〉所见的“卫叔封”》,收入《简帛文献考释论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83—87页。朱凤瀚《清华简〈系年〉所记西周史事考》,李宗焜主编:《出土材料与新视野》,台北:中央研究院,2013年,第441—460页。熊贤品《〈清华简(伍)〉“汤丘”即〈系年〉“康丘”说》,《历史地理》第34辑(2017年),第49—58页。魏栋《论清华简“汤丘”及其与商汤伐葛前之亳的关系》,《中华文史论丛》2017年第1期,第333—354页。
[6] 〔清〕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卷四,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136页。
[7]《史记·周本纪》载:“武王至于周,自夜不寐。周公旦即王所,曰:’曷为不寐?’王曰:’…… 维天建殷,其登名民三百六十夫,不显亦不宾灭,以至今。我未定天保,何暇寐!’“司马迁所述就是根据《逸周书·度邑》。黄怀信、张懋镕、田旭东:《逸周书汇校集注》卷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467—471页。
[8] 徐中舒:《西周史论述(上)》,《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3期,第94页。
[9]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854页。
[10] 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观堂集林》卷十,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452页。
[11] 吕思勉著:《先秦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第123页。
[12]《尚书·多士》中载周成王平叛后,还对殷遗民训话说:“尔殷遗多士!弗吊旻天,大降丧于殷。”。
[13] “鄁”元刊本作“酇”,余诸本作“郑”。陈逢衡、陈星垣、孙诒让等认为应是“郒”之误。黄怀信等:《逸周书汇校集注》卷五,第510页。
[14] 蒙文通:《古史甄微》,收入《蒙文通全集》第3册,成都,巴蜀书社,2015年,第105页。
[15]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清嘉庆刊本),卷二,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622页。
[16] 陈启源:《毛诗稽古编》卷三,阮元、王先谦编:《清经解?清经解续编》(第一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4年,第353页。
[17] 段玉裁注,许惟贤整理:《说文解字注》,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年,第207页。
[18] 朱鹤龄着,虞思征编:《愚菴小集》卷十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37页。
[19] 孙作云遗作:《说豳在西周时代为北方军事重镇——兼论军监》,《河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1期,第41页。
[20] 李民:《蔡国始封与蔡姓始祖溯源》,《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与进程》,北京:线装书局,第206页。
[21] 先秦时期,军队驻扎点往往容易形成都市。如西周铜器兮甲盘(《集成》10174)载:“淮夷旧我帛晦人,毋敢不出其帛、其积、其进人、其贾,毋敢不即次即市。“”即次即市“李零认为即指在军队驻地附近所设军市。《孙子兵法?作战》:“近师者贵卖。“李零说这里的”近师“”指军旅驻扎地附近。案古代往往在军队驻地附近设军市“。李零:《吴孙子发微》,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42—43页。
[22] 许慎撰:《说文解字》,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133页。
[23]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贰)》,第141页。
[24] 西周金文中有“应监”、“鄂监”、“诸侯诸监”等,学者据此对西周监国制度多有讨论(新近的研究可参田率:《新见鄂监簋与西周监国制度》,《江汉考古》2015年第1期,第68—75页; 黄锦前:《叶家山M107所出濮监簋及相关问题》,《四川文物》 2017年第2期,第71—75页)。任伟根据金文认为,周初的“三监”是监于外,具有军事据点性质的,可从。任伟:《从“应监”诸器铭文看西周的监国制度》,《社会科学辑刊》2002年第5期,第103页。
[25] 黄怀信等:《逸周书汇校集注》卷五,第510,512页。
[26] 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卷二十八下,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647—1648页。
[27]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清嘉庆刊本),卷二,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622页。
[28] 司马迁撰,裴轧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史记》卷四,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163页。
[29] 司马迁撰,裴骃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史记》卷三,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163页; 方诗铭、王修龄:《古本竹书纪年辑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31页。
[30] 陈奂:《诗毛氏传疏》卷三,阮元、王先谦编:《清经解 清经解续编》(第十册),第1064页。
[31] 顾颉刚:《周公东征史事考证——甲 三监人物及其疆地》,《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十(上),第621、636页。
[32] 王国维:《北伯鼎跋》,《观堂集林》卷十八,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885页。
[33] 许印林说见吴式芬《攈古録金文》引; 方濬益:《缀遗斋彝器款识考释》。转引自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上),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77页。
[34] 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上),第358页。
[35] 王毓彤报道说铜器出土于1962年12月5日,李健订正当为1961年12月5日在万城出土。王毓彤:《江陵发现西周铜器》,《文物》1963年第2期,第53页; 李健:《湖北江陵万城出土西周铜器》,《考古》1963年第4期,第225页。
[36] 郭沫若:《跋江陵与寿县出土铜器群》,《考古》1963年第4期,第181页。
[37] 如陈梦家指出“北子器出江陵,与邶伯之北不同,北子器应属西周初楚之与国之器”。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上),第78页。刘彬徽也认为此北子与中原邶国不同。李学勤也指出,将“北子”与邶、鄘、卫之邶联系,从历史地理知识角度考虑是有困难的,他认为,“北子”之“北”当释为“别”。刘彬徽:《湖北出土两周金文国别年代考述》,《古文字研究》第13辑,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42页; 李学勤:《长子、中子和别子》,《故宫博物院院刊》2001年第6期,第2—3页。
[38] 杨宽:《西周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31页。
[39]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贰)》(下册),第141页。
[40] 朱熹集注:《诗集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47页。
[41] 陈立撰,吴则虞点校:《白虎通疏证》卷四,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161页。
[42] 许慎撰:《说文解字》,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133页。
[43] 于省吾说:“鄙意以为’邶’,金文作’北’,以其在殷都安阳之北,故以为名。邶之为国,当在燕之南与殷之北,即今河北省南端。“于省吾说为顾颉刚引:《周公东征史事考证》之《甲 ”三监“人物及其疆地》,《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十(上),第631页。
[44] 杨筠如撰,黄怀信标校:《尚书覈詁》卷二《盘庚上》,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第142页。
[45] 顾颉刚:《周公东征史事考证》之《“三监”人物及其疆地(周公东征事考证之一)》,《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10(上),第631—632页。
[46] 杨宽:《西周史》,第132—133页。
[47] 晁福林:《诗经学史上的一段公案——兼论消隐在历史记忆中的邶、鄘两国》,《历史文献研究》总第27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49页。
[48] 陈槃:《春秋大事表列国爵姓及存灭表譔异续编(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60年第31本,第28—29页。
[49] 雷学淇:《介庵经说》,收入《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卷三《诗说》,第97页。
[50] 韦心滢:《殷代商王国政治地理结构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163页。
[51] 郑振香:《论殷墟文化分期及其相关问题》,“中国考古学研究”编委会编:《中国考古学研究: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年纪念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年,第126—127页;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殷墟的发现与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37—39页。
[52] 1979年安阳考古队将殷墟第四期墓葬分为五小段,20世纪80年代以后考古工作者认为将第四期墓葬分为五小段是可以成立的,这五小段分别以IV1、IV2、IV3、IV4、IV5称之。唐际根、汪涛:《殷墟第四期文化年代辨微》,《考古学集刊》(15),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第36—50页。
[53] 唐际根、汪涛:《殷墟第四期文化年代辨微》,第44页。
[5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殷墟的发现与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58,66页。
[55] 石璋如:《小屯?北组墓葬》,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1970年; 石璋如:《小屯·中组墓葬》,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1972年。转引自杨锡璋、高炜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中国考古学·夏商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353页。
[56] 杨锡璋、高炜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中国考古学?夏商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355页。
[5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殷墟的发现与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66页。
[58] 郑振香:《安阳殷墟大型宫殿基址的发掘》,《文物天地》1990年第2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殷墟大型建筑基址的发掘》,《考古》2001年第5期,第25—26页。
[59] 杨锡璋:《安阳殷墟西北冈大墓的分期及有关问题》《中原文物》1981年第3期,第52页; 杨锡璋:《商代的墓地制度》,《考古》1983年第10期,第930页; 杨锡璋:《关于殷墟初期王陵问题》,《华夏考古》1988年第1期,第86—94页。
[60] 杨锡璋:《商代的墓地制度》,《考古》1983年第10期,第930页; 井中伟:《殷墟王陵区早期盗掘坑的发生年代与背景》《考古》2010年第2期。第78—79页。
[6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殷墟的发现与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120页。
[62] 杨锡璋、杨宝成:《从商代祭祀坑看商代奴隶社会的人牲》,《考古》1977年第1期,第15页。
[6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殷墟发掘报告(1958—1961)》,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年,第265—279页。
[64] 杜金鹏:《安阳后冈殷代圆形葬坑及其相关问题》,《考古》2007年第6期,第76—89页。
[65] 裘锡圭(署名赵佩馨):《安阳后岗圆形葬坑性质的讨论》,《考古》1960年第6期,第35页。
[66] 《诗古微》上编之三《邶鄘卫义例篇上》,魏源:《魏源全集》,长沙:岳麓书社,2004年,第215页。
[67] 陈奂:《诗毛氏传疏》卷三,第1064页。
[68] 唐兰:《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22页。
[69] 黄怀信等:《逸周书汇校集注》卷四,第421页。
[70]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卷十四,第436页。
[71] 张桂光:《沬司徒疑簋及其相关问题》,《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二辑),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68—69页。
[72]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贰)》(下册),第145页。
[73] 李泰等撰,贺次君辑校:《括地志辑校》,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87、89页。
[74] 李吉甫撰,贺次君点校:《元和郡县图志》,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460、461页。
[75] 高士奇撰:《春秋地名考略》,清康熙间钱塘高氏刻本,贾贵荣、宋志英辑:《春秋战国史研究文献丛刊》(3),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第301页,
[76] 《嘉庆重修一统志》(12)卷二〇一,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9824页。
[77] 郑杰祥:《商代地理概论》,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30页。
[78] 郭宝钧:《濬县辛村》,北京:科学出版社,1964年,第72页。
[79] 孙华:《周代前期的周人墓地》,《远望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华诞四十周年纪念文集》,西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年,第277页。
[80] 韩朝会、高振龙:《河南淇县杨晋庄发现西周卫国墓群》,《中国文物报》2017年6月30日,第8版。
[81]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卷二,第622页。
[82] 陈奂:《诗毛氏传疏》卷三,第3997页。
[83] 刘师培著:《周书补正》卷三,收人氏著《刘申叔遗书》,上册,南京,凤凰出版社,1997年,第747—749页。
[84] 杜佑撰,王文锦、王永兴、刘俊文、徐庭云、谢方点校:《通典》卷一七八,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4695页。
[85] 乐史撰,王文楚等点校:《太平寰宇记》卷五六,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153页。
[86] 关于周武王克商后的享年,历来说法不一,有二年、三年、六年、七年、八年诸说。根据《尚书·多方》,六年以上诸说均不可信。清华简《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相当于今本《金滕》)载:“武王既克殷三年,王不豫有迟”,与传世今本《尚书·金滕》“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说法相异; 彭裕商认为,简本说法与《多方》等诸多文献相矛盾,因此当以传世今本为优。笔者认为彭说可从,当以“二年”说可信。参唐兰:《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第3—4页;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下册),上海:中西书局,2010年,第158页; 彭裕商:《〈尚书·金滕〉新研》,《历史研究》2012年第6期,第157—158页。
[87] 陈寿祺辑校:《尚书大传》卷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01页。
[88] 朱凤瀚:《〈召诰〉、〈洛诰〉、何尊与成周》,《历史研究》2006年第1期,第13页。
[89] 陕西省文物局、中华世纪坛艺术馆:《盛世吉金——陕西宝鸡眉县青铜器窖藏》,北京,北京出版社,2003年,第30—35页。
[90] 夏含夷,《周公居东新说———兼论〈召诰〉、〈君奭〉著作背景和意旨》,《古史异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第307页。
[91] 张光裕,《簋铭文与西周史事新证》,《文物》2009年第2期,第53—56页。
[92] 陈寿祺辑校:《尚书大传》卷二,第101页。
[93] 盈、嬴古通,如《左传》楚蒍贾字伯嬴,《吕氏春秋》作“盈”。黄怀信等:《逸周书汇校集注》卷五,第515页。
[94] 此“三年”所指古今学者争论很大,具体可参焦循《孟子正义》、杨伯峻《孟子译注》。今人金景芳认为应指“周公东征三年”,由清华简《系年》可知金氏说成立,周公东征仍为成王纪年,故应为周成王三年。焦循:《孟子正义》,卷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449—451页; 杨伯峻:《孟子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158页; 金景芳,《中国奴隶社会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18页。
[95] 李学勤:《纣子武庚禄父与大保簋》,《甲骨文与殷商史(新二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4页。按,彔子耿本作彔子。徐中舒认为“彔”是国名(徐中舒:《西周史论述》(上),第95页),这是正确的。“彔子”之称如同“微子”、“箕子”的称谓,关于“微”、“箕”,东汉马融说:“微、箕,二国名。“(何晏注引,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论语注疏》卷一八,第5494页。)郑玄也说:“微与箕,俱在圻内。“(郑注见《书疏》及《论语·微子篇》皇侃疏,转引自孙星衍撰,陈抗、盛东铃点校:《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九,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53页)因此,”彔“也是国名。唐兰说:“彔子之国当在今河北省平乡县一带,…… 在殷虚之北,约100余公里,王子禄父北奔,当即至此。“(唐兰:《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第74页。)当是。应该是名,而武庚则是日名(或庙号)。周人习称“某父”,故“禄父”应该是周人对武庚的称呼。
[96] 清代学者陈乔枞说:“据韦昭解’侯卫’引《康诰》云云,则知《大传》所云’四年建侯卫’即此《经》’侯、甸、男、邦、采、卫’。’侯卫’者,总侯圻至卫圻包五服而言之。五服之人,即事于周者,公皆勉劳之也。“陈乔枞:《今文尚书经说考》卷七五《康诰》,阮元、王先谦编:《清经解 清经解续编》(第十一册),第1091页。现代学者金景芳也说“建侯卫”“其主要内容是封宋、封卫、封鲁、封齐、封燕”,这说明就是普遍分封。见金景芳:《中国奴隶社会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18页。或将“建侯卫”理解为分封卫康叔,根据清华简《系年》可知这是不对的。《系年》第四章:“周成王、周公既迁殷民于洛邑,乃追念夏商之亡由,旁设出宗子,以作周厚屏; 乃先建卫叔封于康丘“; 《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载周大夫富辰劝谏周襄王说:“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东汉马融、晋代杜预均认为”二叔“指”夏、殷叔世“; 故二者可互证,而前者“周成王、周公既迁殷民于洛邑,乃追念夏商之亡由,旁设出宗子,以作周厚屏”正对应于后者所谓的“封建亲戚,以蕃屏周”,即普遍分封诸侯之义。(详参拙文:《清华简〈系年〉与〈左传〉互证二则》,《文史》2015年第4辑,第264—269页)因此封康叔在普遍分封诸侯之“先”,且据本文考证,封康叔实际上在周成王二年(详后文)。
[97] 黄怀信等:《逸周书汇校集注》卷五,第518页。
[98] 金兆梓著:《尚书诠译》,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308—309页。
[99] 贾逵说见孔颖达《尚书正义?多士》篇引,《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卷十六,第466页;
[100] 《汉书?地理志》卷二十八,第1647页。
[101] 《帝王世纪》说为张守节《史记?刘敬传》正义转引《括地志》,作“《尚书〔序〕》曰’成周既成,迁殷顽民’。《帝王世纪》云’居鄘之众’“《校堪记》曰:”疑”当作’邶’“,证据是””,彭本、《会注》本作’邶’。黄本作’郐’,同’邶’“。笔者认为此校堪无疑是正确的:一者有版本依据; 二者除此作“鄘”外,其他文献均作“邶鄘”或“郏鄘”,且、邶形近易讹,此处应为形讹。但《校堪记》又曰:“疑鄘下脱’邶’字”,所列出证据为《史记?周本纪》张守节《正义》,其曰“《尚书?洛诰》云:’我卜瀍水东,亦惟洛食’,以居邶鄘卫之众”。笔者以为,此处校堪似是而实非:第一,张守节所引文,前半部分“我卜瀍水东,亦惟洛食”见于今本《尚书·洛诰》文,作“我又卜瀍水东,亦惟洛食”; 而后半部分“以居邶、鄘、衞之众”纯为张氏个人说法。表面上看《正义》“居邶、鄘、卫之众”与《帝王世纪》“居邶鄘之众”近似,其实二者绝不同,因为前者是张守节个人的说法,而后者是《帝王世纪》之文,因此前者绝非后者之版本依据。第二,退一步说,假若张守节《正义》所说为是,那么证据何在呢?张守节说:“武王灭殷国为邶、鄘、卫,三监尹之。武庚作乱,周公灭之,徙三监之民于成周,颇收其余众,以封康叔为衞侯,卽今衞州是也“。可见,张氏认为周公平叛后,将邶、鄘、卫三监之民迁到成周,但这种说法实际上是错的,因为据东汉贾逵《左传解诂》与班固《汉书·地理志》均谓所迁民仅仅为邶、鄘之民而无卫众,故张守节所说不成立。总之,《校堪记》谓“《帝王世纪》”居鄘之众“应作”居邶鄘之众“无疑是正确的,但说”鄘“后脱”卫“实乃蛇足。需要指出的是,《校堪记》所谓“疑鄘下脱’邶’字”的说法实乃根据贺次君之说。贺次君《括地志辑校》作《帝王世纪》云“居邶鄘(卫)之众”,其证据是“《帝王世纪》本《尚书?洛诰》,脱’卫’字,今据《尚书》补”,按贺氏所谓《帝王 世纪》根据《尚书?洛诰》是错误的,前文已述“以居邶、鄘、卫之众”并非《尚书?洛诰》文而实为张守节之语,故贺次君所补亦非。又,徐宗元辑《帝王世纪辑存》作“(周公营成周,)居邶鄘之众”,这是正确的。司马迁:《史记》,第3291,3302,170页; 贺次君:《括地志辑校》卷三,第169页; 徐宗元辑:《帝王世纪辑存》,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第91页。
[102] 关于所迁者为何仅为邶、鄘之民,清代学者王鸣盛解释说:“邶既纣子武庚所封,鄘乃首倡逆乱,连结武庚之管叔所封,蔡叔但从之而已,故周公杀管叔,放蔡叔,其罪大有重轻。想邶、鄘民皆从乱,即所谓’殷顽民’也,是以迁之于雒,而虚其地,衞民则不迁。康叔尽得三国地,而民则但得衞一国民,其情形如此。“王氏认为迁邶、鄘之民,是因为邶、鄘地分别为武庚、管叔所辖,其民罪重,故迁之。王氏之说乃根据班固的说法,《汉书·地理志》曰:“鄁,以封纣子武庚; 庸,管叔尹之; 衞,蔡叔尹之:以监殷民“。而由本文考证,管叔所监之地在卫,班固之说实不可信。王鸣盛著,顾美华整理标校:《蛾术编》卷二《说锈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2年,第42页。
[103] 黄怀信等:《逸周书汇校集注》卷五,第520页。
[104] 章太炎《小学答问》曰:“献音古近櫱,音当作牛建切,与鬳同音,入声为櫱。…… 子孙谓之由枫,…… 其以民言,亦谓之庶,亦谓之蘖。…… 元在寒部,与献同音。字或为顽。…… 殷献民者,殷栌民……。余民,故谓之栏民……。《多士序》:’成周既成,迁殷顽民。’殷顽民,即殷献民,皆栏民也。故其书曰:’尔殷遗多士。’迁殷顽民于成周,与迁殷献民于九里,其事相因。孙诒让据《战国策》、《韩非子》谓九里亦作臼里,地在孟津,为东周畿内地。盖雒邑未成以前,迁之畿内; 既成以后,乃迁成周。足知献民、顽民非二。“章太炎:《小学答问》,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蒋礼鸿,殷孟伦,殷焕先点校:《章太炎全集》(第七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494—495页。周厉王的胡簋曰:“肆余以…… 士献民“,张政烺认为:”献民即仪民,乃殷之故家世族也。“张政烺:《周厉王胡簋释文》,《古文字研究》第3辑,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08页。
[105] 于鬯说:“殷之狱称里,故文王所囚曰’牖里’。’九里’与’牖里’,论音亦近,固不必附会,而九里者傥亦本是狱名,因为地名者与。《公羊》昭二十一年《传》云:’宋南里者何?若曰因诸者然。’何休《解诂》云:’因诸者,齐故刑人之地。’公羊齐人,故以齐喻。徐彦解引《博物志》云:’周曰囹圄,齐曰因诸,然则南里亦狱名矣。’宋殷后,犹名’狱’为’里’,此又殷狱名里之一证也。…… 然则《国策》言’九里’者,固为地名之称;《周书》言’九里’者,本其狱名之称;又同中之异。“于鬯:《香草校书》卷九,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187页。
[106] 别本作“九毕”,王念孙据《玉海》认为后者当为前者之讹,当作“九里”。《战国策·韩策》:“魏王为九里之盟。“又作”臼里“,故《韩非子·说林》作:”魏惠王为臼里之盟。“”九“、”臼“古音很近相通。杨宽认为九里在今河南巩县南七十里的九山下。参黄怀信等:《逸周书汇校集注》卷五,第518—519页; 杨宽:《西周史》,第541页。
[107] 于鬯说:“’俘殷献民迁于九里’,其殆《书·多士序》所称’迁殷顽民’者,’顽民’而谓之’献民’,即《洛诰》云’其大惇典殷献民’,亦安见其非即顽民邪?盖《周书》本无顽民之称,序《书》者言之,著其实而已。(《大诰》云:’民献有十夫。’伏生《大传》’献’作’仪’。’仪’之言’义’也,然则献民即义民矣。在周为顽,即在殷为义。)要非顽民,何以俘之迁之?既俘之、迁之而禁锢之,此固事势之必然者矣。“于鬯:《香草校书》卷九,第187页。
[108] 关于成周开始营建与建成的时间,关涉到《尚书》中的《多士》、《召诰》、《洛诰》的制作年代以及1963年出土何尊的年代,长期以来学者意见分歧。根据现有数据,笔者认为成王三年就开始营建成周。至于成王五年三月召公才开始所卜、营建之宅,唐兰、朱凤瀚等学者认为是周成王的居住宫室,十二月,成周的大规模建筑已经完工。可参唐兰:《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第18页。朱凤瀚:《〈召诰〉、〈洛诰〉、何尊与成周》,第5页。段渝:《〈多方〉〈多士〉的制作年代及诰令对象》,《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1期,第96页; 杨宽:《西周史》,第531—534页; 彭裕商:《西周青铜器年代综合研究》,成都,巴蜀书社,2003年,第36页。
[109]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卷一六,第466页。
[110] 徐昭峰:《成周与王城考略》,《考古》2007年第11期,第69页。
[111] 叶万松、张剑、李德方:《西周洛邑城址考》,《华夏考古》1991年第2期,第74页。
[112] 张剑:《洛阳两周考古概述》,叶万松主编、洛阳文物考古队编:《洛阳考古四十年——1992年洛阳考古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16—17页。
[113] 郭宝钧、林寿晋:《一九五二年秋季洛阳东郊发掘报告》,《考古学报》第九册(1955年第1期),第96,97,103页。
[114] 张剑:《洛阳两周考古概述》,第16—17页。
[115] 洛阳博物馆:《洛阳北窑村西周遗址1974年度发掘简报》,《文物》1981年第7期,第52—64页;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1975—1979年洛阳北窑西周铸铜遗址的发掘》,《考古》1983年第5期,第431—441页。
[116] 洛阳文物工作队:《洛阳西周考古概述》,《西周史研究》,西安:人文杂志编辑部,第355—358页; 唐际根、汪涛:《殷墟第四期文化年代辨微》,第41页。
[117] 唐兰:《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第22页。
[118] 李学勤:《由清华简〈系年〉重释沬司徒疑簋》,第84页。
[119] 阮元,《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卷一七,第3974页。
[120] 《左传》昭公四年:“或无难以丧其国,失其守宇。“孔疏:”宇谓屋檐也。于屋则檐边为宇也,于国则四垂为宇也。四垂谓四竟(境)边垂。“阮元,《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卷四二,第4415页。
[121] 孙诒让从“声类求之,乃知其即康叔之子康伯也”,其引《世本》康伯名髦(今本髦作“髡”,梁玉绳据杜预《春秋释例?世族谱》校正),东汉末的宋忠认为即《左传》昭公十二年的王孙牟,司马贞也说牟、髦声相近。孙诒让认为旄与髦是同声假借字,中旄父即王孙牟。孙诒让撰,雪克点校:《籀庼述林·邶鄘卫考》卷一,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10页。刘师培也认为:“以中旄父为康伯,其说至确。“刘师培著:《周书补正》卷三,《刘申叔遗书》,第748页。
[122] 阮元:《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卷五四,第4636页。
[123] 郭宝钧:《中国青铜时代》,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第45页。
[12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殷墟的发现与研究》,第78—92,407—409页; 刘庆柱主编:《中国考古发现与研究(1949—2009)》,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42—243页。
[125] 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卷四,页3764。
[126] 有学者认为“先”当读为“选”,以《左传》定公四年“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选建明德,以蕃屏周”相比附(李天虹:《小议〈系年〉“先建”》,《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李学勤先生八十寿诞纪念论文集》,上海:中西书局,2016年,第264—266页。)实际上,“选”《说文?辵部》:“一曰选,择也。“《左传》之”选建明德“强调从众多的人中按照明德的标准选出好的来。而《系年》之“先建”显然表示先后之义,两者不可混同。
[127] 值得注意的是,今本《竹书纪年》曰:“(成王)三年,王师灭殷,杀武庚禄父,迁殷民于卫。“王国维考证此处今本作者乃根据《逸周书?作雒》:”二年,又作师旅,临卫政殷,殷大震溃。降辟三叔,王子禄父北奔。“黄凡认为,今本所谓”灭殷“及”迁殷民于卫“其实是成王二年事,今本误置于三年。黄说主要依据今本《纪年》,而今本学界多认为后人伪托,但其中有些说法可能来源较早,故黄说虽无坚实根据,但观点却歪打正着。王国维:《今本竹书纪年疏证》,载于方诗铭、王修龄撰:《古本竹书纪年辑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244页。黄凡:《〈竹书纪年〉——利用〈周易〉辨误》,邵东方、倪德卫主编《今本竹书纪年论集》,台北:唐山出版社,2002年,第353页; 原载黄凡著:《周易——商周之交史事録》,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360页。
[128] 李学勤:《由清华简〈系年〉重释沬司徒疑簋》,第84页。此观点又见氏著《清华简〈系年〉及有关古史问题》(第73页)、《清华简〈系年〉解答封卫疑谜》(第15页)两文。后二者与前文相比语气有微小变化,但基本观点一致。
[129] 朱凤瀚:《清华简〈系年〉所记西周史事考》,第449页。
[130] 路懿菡:《从清华简〈系年〉看康叔的始封》,《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第139页; 路懿菡:《清华简与西周史研究》,西安:三秦出版社,2018年,第152页。
[131] 比如清代学者顾栋高说:“(康叔封)国于朝歌,今河南卫辉府淇县东北有朝歌城。“顾栋高辑,吴树平、李解民点校:《春秋大事表》卷五,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564页。
[132] 司马迁,《史记》,卷七,第1册,第396页。
[133] 李学勤:《由清华简〈系年〉重释沬司徒疑簋》,第85页。朱歧祥认为“淇卫”二字连用,古书罕见水名与地名并连的,并进而怀疑《系年》之真实性。对此黄泽钧已指出《系年》简83的“柏举”是柏水与举洲的并连,而柏举古书常见,所以朱氏的怀疑并不成立。朱歧祥:《谈清华简(贰)〈系年〉的“卫叔封于康丘”句及相关问题〉,《东海中文学报》第29期,2015年6月,第176页。黄泽钧:《清华简〈系年〉地名构词研究》,发表于第十八届中区文字学学术研讨会,台中:东海大学,2016.05.21—22。
[134] 顾颉刚,《顾颉刚读书笔记》(收入《顾颉刚全集》),卷七,第151—152页。
[135] “侯”与“候”本一字分化,汉代人普遍把“侯”训为“候”,《白虎通?爵》:“侯者,候也”等。可参:劳榦:《“侯”与“射侯”后记》,中华书局编辑部编:《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论文类编·历史编·先秦卷》,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297页。简文之“侯”当作“候”,动词。《吕氏春秋·贵因》:“武王使人候殷。“高诱注:”候,视也。“简文此处不仅有监视的意思,还有监管、管理的意味。
[136] 皮锡瑞,《今文尚书考证》(北京:中华书局,1989),第319页。
[137] 此处的《康诰》即今文《尚书·康诰》,是周成王四年卫人迁徙时,周公代成王命康叔的诰辞; 而前引《左传》定公四年所谓的《康诰》,乃成王二年封康叔于康丘的命书。详参拙文,《清华简《系年》与《尚书·康诰》诸问题新探》,待刊。
[138] 《史记·卫康叔世家》载卫顷侯前六代皆称“伯”,顷侯时“厚赂周夷王,夷王命卫为侯”。董珊据此认为迟至卫顷侯时“康侯”始称“卫侯”,见董珊,〈清华简《系年》所见的「卫叔封」〉,《简帛文献考释论丛》,页84。实际上,《史记》此处所载谓卫由“伯”变成“侯”,而非由“康”变成“卫”,二者不同; 董氏此说实乃曲解《史记》文,不可从。事实上,由金文可见,早在康叔时期已经称「侯」,故《史记》此说盖亦不可信。
[139] 陈启源:《毛诗稽古编》卷三,阮元、王先谦编:《清经解 清经解续编》(壹),第353页。
[140] 孙诒让撰,雪克点校:《籀庼述林·邶鄘卫考》卷一,第10页。
[141] 熊贤品:《〈清华简(伍)〉“汤丘”即〈系年〉“康丘”说》,第49—58页; 魏栋:《论清华简“汤丘”及其与商汤伐葛前之亳的关系》,第339页。
[142]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与保护中心编、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伍)》,上海:中西书局,2015年,第135页。
[143] 如郭店简《绳衣》简5“惟伊允及汤”,上博简《绳衣》“汤”作“康”; 上博简《曹沫之阵》简65“亦唯闻夫禹、康(汤)、桀、纣”,“康”读为“汤”。白于蓝编著:《战国秦汉简帛古书通假字汇纂》,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71、705页。
[144] 黄灵庚疏证:《楚辞章句疏证》卷五,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423页。
[145] 《吕氏春秋·慎大》:“武王乃恐惧,太息流涕,命周公旦进殷之遗老,而问殷之亡故,又问众之所说、民之所欲。殷之遗老对曰:’欲复盘庚之政。’武王于是复盘庚之政。”
[146] 姚鼐着:《惜抱轩笔记》卷四《史部一》,《惜抱轩全集》,北京:中国书店,1991年,第558—559页。
[147] 潘明娟:《从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的关系看早商的主都和陪都》,《考古》2008年第2期,第55—63页。
[14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发掘报告(1958—1961)》,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年,第61—64页。
[149]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发掘报告(1958—1961)》,第64—69页。
[150] 刘一曼:《安阳小屯西地的先商文化遗存——兼论“梅园庄一期”文化的时代》,《三代文明研究(一)——1998年河北邢台中国商周文明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148—161页。
[151] 刘一曼:《安阳小屯西地的先商文化遗存——兼论“梅园庄一期”文化的时代》,第148—161页。
[152] 中美洹河流域考古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科技考古实验室):《洹河流域区域考古研究初步报告》,《考古》1998年第10期,第21页。
[153] 这里我们需要明确指出的是,清华简虽然说“汤丘”是商王成汤所旧居,在殷墟也发现了先商和商早期的文化遗存; 但不可否认的是,清华简所载只是战国时期的一种记载,成汤是否真居于此,根据现有材料还难以考定。唯一可以确定的是,战国时期确实流传着这种说法。
[154] 朱骏声:《尚书古注便读》卷四中,新北:花木兰文化出版社, 2013年,第125页。
[155] 皮锡瑞撰; 盛冬铃,陈抗点校:《今文尚书考证》卷十四,第306页。
[156]《尚书·康诰》伪《孔传》:“封,康叔名”,“叔,封字。“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卷十四,第430—431页。
[157] 马融说为孔颖达《正义》引,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卷十四,第430页。
[158] 王肃说见孔颖达所引,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卷二,第623页。
[159]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卷十四,第430页。
[160] 孔颖达说:“惟郑玄以’康’为谥号。“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卷十四,第430页。
[161] 杨锡璋、商炜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中国考古学·夏商卷》,第294—295页; 何毓灵、岳洪彬:《洹北商城十年之回顾》,《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1年第12期,第15页。
[162] 王国维:《说殷》,《观堂集林》卷十二,第525页。
[163] 唐际根:《殷墟一期文化及其相关问题》,《考古》1993年第10期,第933页。
[16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殷墟的发现与研究》,第50页。
[165] 简朝亮:《尚书集注述疏》卷十二《洪范》,《尚书类聚初集》(4),台北: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4年,第71页。
[166] 陈寿祺辑校:《尚书大传》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54页。
[167] 王闿运补注:《尚书大传补注》卷五,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37页。
[168] 陈剑:《甲骨金文“”字补释》,氏著:《甲骨金文考释论集》,北京:线装书局,2007年,第99—106页。
[169] 陈寿祺,《尚书大传》,卷二,第83页。
[170] 张光裕:《簋铭文与西周史事新证》。
[171] 李学勤:《何簋与何尊的关系》,《出土文献研究》(第九辑),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2页。
[172] 井中伟:《殷墟王陵区早期盗掘坑的发生年代与背景》,第78—90页。
[173] 石璋如:《殷墟最近之重要发现附论小屯地层》,《中国考古学报(即田野考古报告)》第二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1947年,第14—15页。
[174] 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卷四,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114页。
[175] 陈启源:《毛诗稽古编》卷三,阮元、王先谦编:《清经解 清经解续编》(壹),第3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