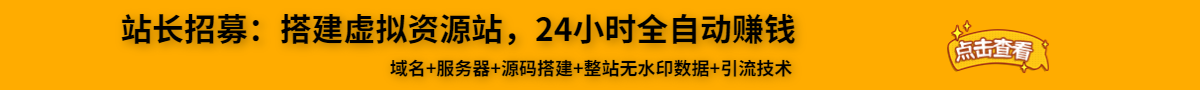导演们对现实主义的理解太局限了。现实主义的厉害之处在于“真实”,在大家可感可知的范围内。(东方IC/图)
(本文首发于2018年6月21日《南方周末》)
我小时候很少有机会坐公交车,倒是经常看着公交车从村口驶过,扬起长久的尘土。有一次,母亲带我去市里,我非常高兴,窗外的世界让我看不够。返回时却因无聊而发脾气。小孩子就这样。母亲见我撒泼耍赖,就让我看窗外。来的时候我一直趴在窗口看也看够了。所以,我也不听她的话,继续大哭。后来,那辆破烂的11路公交车就行驶在了一片水塘边上的小路上。
这时,母亲忽然手指着窗外,说:“你看,那边,从这往那边看,你看到了么?”我看到一根斜插在水中的木棍。母亲又说:“那可不是用来打鱼的。”我很奇怪。她继续说:“正琢磨着把我这不听话的孩子放回去,因为她就是从那把你捡来的。”我紧张地转头,透过车窗,向她手指的方向,精神专注起来。
我一直记着这个事,想想觉得幼稚可笑。工作以来,却觉得意味深远,直到有机会进剧组学习。很多导演、摄影师都跟我说过类似的话,剔除那些中景、视角、中轴线、眼神光等等名词,剩下的,简直和这段童年记忆不谋而合。
什么人想什么事,看事就是思考的角度。也许,母亲就可以说成是一个有导演思维的人吧。多年之前,她就在窗外给我指出过这个道理——一个作者就这么回事。写下去,拍出来,也许微小,但能令人动容,因为这里面充满了情感的交流。从我离开村子,见到街头这么多的人吓一跳之外,就得慢慢地,带着热情和大家相处下来。很多人不是无法战胜别人,我认识很多厉害的作家、导演深陷焦虑,他们不是想不通,而是无法原谅自己,自己都被自己耻笑的感觉很不好。
最近,一些朋友们聚会,都会提到电影院扎堆的犯罪题材,三个编剧有两个在写犯罪题材,五个公司有四个公司在谈犯罪类型片的出路。
导演们对现实主义的理解太局限了。现实主义的厉害之处在于“真实”,在大家可感可知的范围内。其实“犯罪”“真实案件改编”等不一定比市井吵架、小情侣恋爱马拉松现实主义。因为,“犯罪事件”在我们——导演和观众的认知程度上相差无几,网络时代是个失去绝对讲述权利的时代。远了说,古代水手,1980年代的小说家,都具有故事的讲述权利。我们不知道的,他知道。
现在,连我母亲也不是我小时候那个故事能手了。她说起故事时断时续,包括词语都有所筛选,一个发生在我们村的人命案,在她的口中,还不如我小时候听她讲自己养猫的故事生动。
最近一次,我和母亲又在下午乘坐公交车从市里返回,母亲再次给我指出一片野地,我的目光迅速变成一个荒凉的医院全景。她说:“听说这里的医院要搬到我们家那边,这块地原来是地震时期填死人的,这种地方都得镇得住的单位才行……”车窗外移动的病房在近景中偶尔有几个亮灯的房间,的确很冷清。我等着她说话,她却停止不说,看着我,问:“这事你不知道吧?”
这是新变化,视角没有拯救故事,是谁的问题呢?
有时候,观点是新的,方式还是老的好。电影圈基本上都是老搭档,从导演到摄影,甚至到演员,台湾的侯孝贤导演和摄影师李屏宾、编剧朱天文;国内的冯小刚和演员葛优、作家刘震云;韩国的洪常秀导演总是和那几个人合作等等都是这样。
几个新导演瞎聊,其中几个人问这样做有什么好处。他们觉得,这样死板。我反问,这样做有什么坏处?像我们这些新人不都是在合作中,寻找这有老搭档可能的朋友们吗?老搭档是我小时候和母亲那种交流形式的延续,在公交车上,为窗外的一处风景而产生情绪起伏,就像我们同在现场,为一场戏而挠头挣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