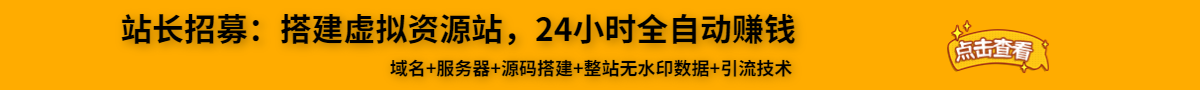一
江歌案中刘鑫(刘暖曦)所涉及的义务
2022年2月16日,江秋莲起诉刘鑫(后改名刘暖曦)案二审开庭。
2016年11月3日,江秋莲的独生女儿江歌在日本东京被刘鑫(刘暖曦)的前男友陈世峰杀害。江秋莲认为,江歌遇害事件中,刘暖曦虽不是直接伤害人,但存在重大过错,且其过错与江歌的死亡结果有直接因果关系,诉至青岛市城阳区人民法院,请求判令刘暖曦赔偿207万余元。
2022年1月10日,青岛市城阳区法院一审宣判,刘暖曦被判赔偿江秋莲69.6万元。法院审理认为,刘暖曦作为江歌的好友和被救助者,对由其引入的侵害危险,未如实向江歌进行告知和提醒,在面临陈世峰不法侵害的紧迫危险之时,为求自保而置他人的生命安全不顾,将江歌阻挡在自家门外而被杀害,具有明显过错,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综合考量本案的事发经过。行为人的过错程度、因果关系等因素,法院对江秋莲主张的有证据支持的各项经济损失,酌情支持49.6万元。
此外,刘暖曦事后发表刺激性言论,进一步伤害了江秋莲的情感,依法应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根据行为情节、损害程度、社会影响,酌情判令刘暖曦赔偿江秋莲精神损害抚慰金20万元。对此,刘暖曦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将案件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江秋莲的全部诉讼请求。
尽管杀害江歌的凶手陈世峰已于2017年在日本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但“江歌案”始终受到相当一部分人的持续关注。因为,另一名焦点人物,江歌案的源头,刘暖曦所引发的争议一直未能平息。一方面,刘暖曦本身始终坚持自己无过错,对于江歌案,自己不应承担责任。另一方面,相当一部分人认为,无论是从道德层面上,还是从法律层面上,对于江歌,基于好友与凶手女友身份的刘暖曦都应负有责任与义务。
对此,援引青岛市城阳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的内容可见一斑:
“……其次,刘暖曦与江歌双方形成一定的救助关系。刘暖曦与江歌为同在日本留学的好友,刘暖曦因与男友陈世峰发生感情纠葛遭到其纠缠滋扰,身陷困境的刘暖曦向江歌寻求帮助,江歌热心给予帮助,接纳刘暖曦与自己同住长达两个月,为其提供了安全的居所,并实施了劝解、救助和保护行为,双方在友情基础上形成了一定的救助关系,作为危险引入者和被救助者,刘暖曦对江歌负有必要的注意义务及安全保障义务。
再者,刘暖曦对侵害危险具有更为清晰的认知。刘暖曦与陈世峰本系恋爱关系,对陈世峰的性格行为特点应有所了解,对其滋扰行为的危险性应有所认知和预判。陈世峰持续实施跟踪、纠缠、恐吓行为,行为危险性逐步升级,在事发当晚刘暖曦也向江歌发送信息称感到害怕,要求江歌在地铁出口等候并陪她一同返回公寓,说明刘暖曦在此时已经意识到自身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对侵害危险有所预知。
最后,刘暖曦未充分尽到注意义务以及安全保障义务。本案中,刘暖曦在已经预知到侵害危险的情况下,没有将事态的严重性和危险性告知江歌,而是阻止江歌报警,并要求江歌在深夜陪同其返回公寓,将江歌引入因其个人感情纠葛引发的侵害危险之中,刘暖曦并没有充分尽到善意提醒和诚实告知的注意义务。案发之时,在面临陈世峰实施不法侵害紧迫危险的情况下,刘暖曦先行一步进入公寓,并出于保障自身安全的考虑将房门关上并锁闭,致使江歌被阻挡在自己居所的门外,完全暴露在不法侵害之下,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之中,从而受到严重伤害失去生命,刘暖曦显然没有尽到社会交往中的安全保障义务。”
需要注意的是,一审法院首先认定了刘暖曦与江歌双方形成一定的救助关系,其次强调了刘暖曦在本案中的身份是“危险引入者和被救助者”,并由此得出结论“刘暖曦对江歌负有必要的注意义务及安全保障义务”。这并非基于具体某一法条,而是基于民法诚实信用基本原则和权利义务相一致原则:在社会交往中,引入侵害危险、维持危险状态的人,负有采取必要合理措施以防止他人受到损害的安全保障义务;在形成救助关系的情况下,施救者对被救助者具有合理的信赖,被救助者对于施救者负有更高的诚实告知和善意提醒的注意义务。本案中,一审法院根据现有证据,认定作为被救助者和侵害危险引入者的刘暖曦,对施救者江歌并未充分尽到注意义务和安全保障义务,具有明显过错,理应承担法律责任,因此对江秋莲主张的有证据支持的各项经济损失酌情支持。
二
刑法上的救助义务
刑法上的救助义务主要表现在对不作为犯的认定上。
根据我国刑法学基本理论,不作为犯罪的作为义务来源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法律明文规定的积极作为义务
法律明文规定的作为义务是不作为犯罪的作为义务的主要来源之一,是指由其它法律规定并由刑法加以认可的义务,这里的法律可以是法律,法规以及规章制度等。但是如果只由其他法律规定,而未被刑法认可,则不能构成不作为犯罪的作为义务。此外,法律明文规定的义务必须是具体的义务,而类似于宪法中所规定的义务等一般性的抽象义务,一般不适合直接作为不作为犯罪的义务前提。比较典型的作为义务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26条规定:“父母对未成年子女负有抚养、教育和保护的义务。成年子女对父母负有赡养、扶助和保护的义务”,本条规定中的义务人一旦拒绝履行义务,情节严重的便可能违反了我国刑法第261条的规定,构成遗弃罪。
(二)职业或者业务要求的作为义务
指一定的主体由于担任某项或者从事某种业务而依法被要求履行的一定作为义务。该类型的作为义务有的规定在法律法规中,也有的规定在具体行业的相关规章制度中。对于这种义务应当注意的是,行为人只有在具有职业或者业务身份的情况下,才具有相关的作为义务。也就是说,只有在具有这种职业或者业务身份的情况下行为人才能构成刑法上的不作为犯罪。在此可援引《中华人民共和国警察法》第21条规定:“人民警察遇到公民人身、财产安全受到侵犯或者处于其他危难情形,应当立即救助。”
(三)法律行为引起的积极作为义务
法律行为如合同行为等,引起一个积极作为的义务(行为人通过合同行为自我创设一个积极作为义务),行为人有义务履行。一般情况下合同一方当事人如果不履行合同所规定的义务,只产生违约的法律后果,并不会产生不作为犯罪的作为义务;只有在合同一方当事人因不履行合同所规定的义务给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造成严重侵害的情况下,这一作为义务才能构成不作为犯罪的作为义务。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819条的相关规定:“承运人应当严格履行安全运输义务,及时告知旅客安全运输应当注意的事项。旅客对承运人为安全运输所作的合理安排应当积极协助和配合。”如果客运合同的承运人未履行安全运输义务,导致旅客的生命安全遭受严重侵害,承运人便有可能构成犯罪,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四)先行行为引起的积极作为义务
先行行为作为不作为犯罪的作为义务是由德国刑法学家斯特贝尔首倡的,1884年的德国判例首次确认了先行行为与法律,契约同样是作为义务的来源。我国刑法界的通说认为先行行为只要足以产生某种危险,就可以成为不作为犯罪的义务来源,而不必要求先行行为具有违法的性质。比如熟悉水性的甲带不懂水性的乙去游泳,在乙不敢下水时,甲为鼓励乙将其一把推入水中,造成乙溺水或受伤,此时甲已经产生了救助乙的作为义务。
对于救助义务而言,主要表现在职业或者业务要求的救助义务以及先行行为引起的积极救助义务这两个方面。对于具有刑法上救助义务的人,有能力救助而不救助进而导致危害结果发生,情节严重的,义务人会涉嫌不作为犯罪。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本身对于职业或者业务要求的救助义务,如第四百一十六条规定:“对被拐卖、绑架的妇女、儿童负有解救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接到被拐卖、绑架的妇女、儿童及其家属的解救要求或者接到其他人的举报,而对被拐卖、绑架的妇女、儿童不进行解救,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负有解救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务阻碍解救的,处二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第四百二十九条规定:“在战场上明知友邻部队处境危急请求救援,能救援而不救援,致使友邻部队遭受重大损失的,对指挥人员,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第四百四十五条规定:“战时在救护治疗职位上,有条件救治而拒不救治危重伤病军人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造成伤病军人重残、死亡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而职业或者业务要求的救助义务也会出现在一些特定职业的法律法规中,《中华人民共和国警察法》第21条规定:“人民警察遇到公民人身、财产安全受到侵犯或者处于其他危难情形,应当立即救助。”《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44条规定:“消防队接到火警,必须立即赶赴火灾现场,救助遇险人员,排除险情,扑灭火灾。”《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174条规定:“船长在不严重危及本船和船上人员安全的情况下,有义务尽力救助海上人命。”《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301条规定:“承运人在运输过程中,应当尽力救助患有急病、分娩、遇险的旅客。”在上述情形中,法律分别赋予了警察、消防队、船长、承运人等主体对相关人员生命上的危难救助义务。这些主体如果不履行这些义务,则有可能构成不作为犯罪。
在实务中,先行行为引起的积极救助义务常见于故意杀人以及交通肇事后逃逸等涉及伤害的罪名的判决中。犯罪嫌疑人因自身先行行为客观上造成了被害人陷入高度危险状态,使其对被害人负有法律上的救助义务。犯罪嫌疑人如不履行救助义务,则有可能导致被害人受伤,死亡等危害后果,应当依法承担刑事责任。
三
关于救助义务的一些思考
侵权责任理论一般认为,救助义务的主体仅限于负有特定职责或义务的主体,其义务来源于法律规定、职业要求及先前行为。法定义务作为保障法律实施的基本措施,往往采取强制手段予以保障实施,并对违反者予以惩处,对违反法定救助义务并造成严重后果的义务人,等待其的往往是不作为犯罪的惩罚。
在过去,对于不负有特定职责或义务的主体,其救助义务仅限于道德义务而非法律义务,如这类主体并未采取合理措施实施救助,也仅仅是遭受道德上的非难,而无须承担法律责任。但是,如今随着社会关系日益复杂化和人们权利意识的加强,法定义务呈现扩展的趋势,如今,义务的来源不仅包括法律的明文规定、职业的要求、行为人的先前行为,还包括作为兜底的诚信原则或公序良俗,而义务的形式也不限于消极的不作为,而是扩大到积极的作为。
遵循善良风俗及日常经验法则而赋予行为人积极的救助义务,乃是为了应对风险加剧的现代社会而提出的新型义务,是指当他人的生命安全等重大人身利益处于危险状态时,根据诚信原则或公序良俗的要求可期待某个人实施的积极的救助义务。即使是不负有特定职责或义务的主体,如果是危险情形发生时唯一可实施救助的人,且具有相应救助的能力和条件,也应履行适当的救助义务,而违反救助义务的,也应承担相应的民事或者刑事责任。同时,江歌案又为我们带来了一个新的角度,即被救助者应对救助者负有的诚实告知和善意提醒的注意义务以及安全保障义务。而当被救助者未能尽到义务,给救助者引入了危险并造成了危害结果时,被救助者又应当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江歌案尚未结束,由此展开的讨论也仍在持续。笔者希望,江歌案所引发的思考,最后并不以个案为结束,而是能够如同8.27昆山持刀砍人正当防卫案一般,成为激活相关法律法规的一个契机。
律师简介